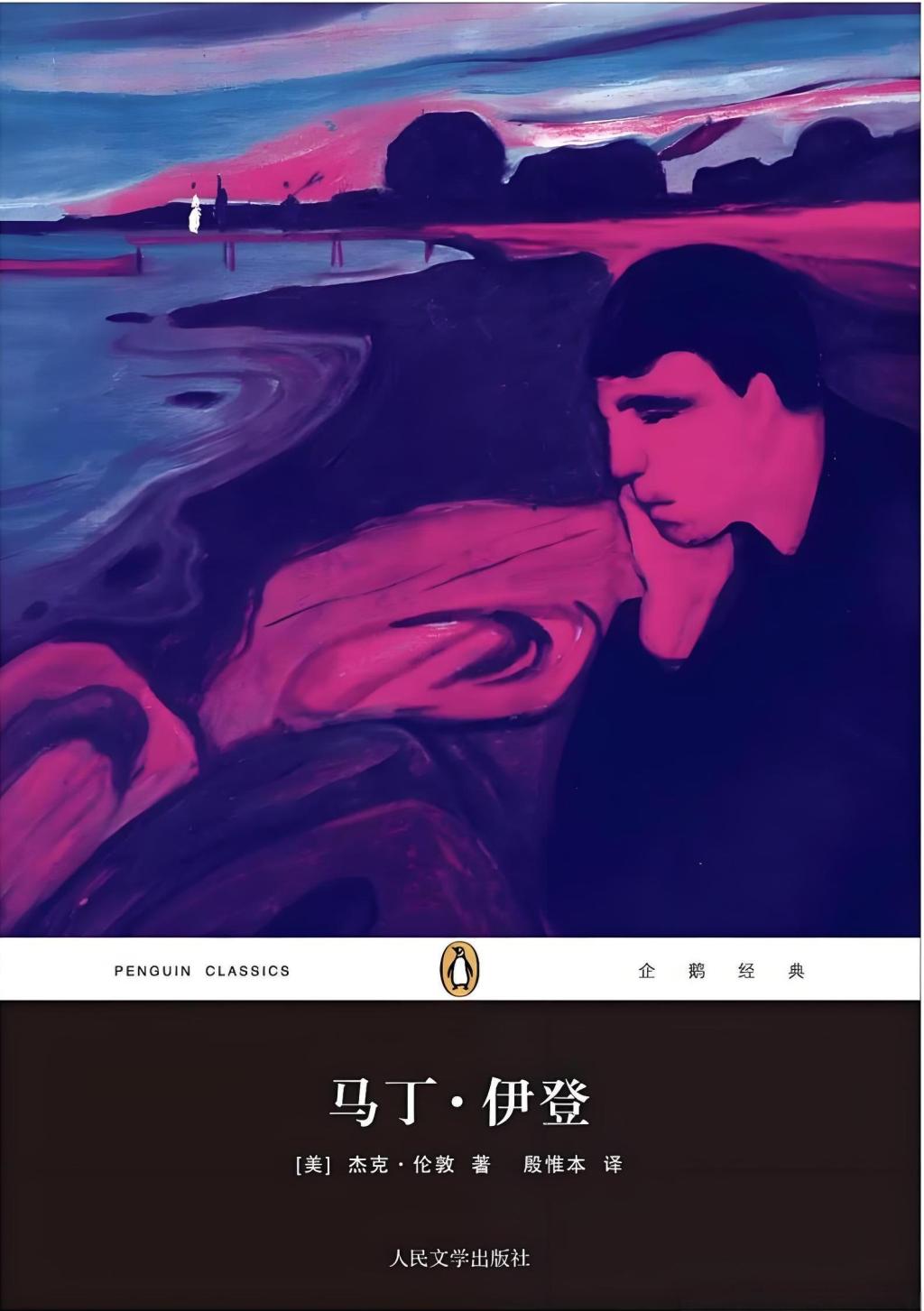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
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û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
ʱ�䣺2018-06-03 04:07:08 ���ߣ���� ��Դ����Ѷ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и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롷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⺭����ʵ˿��û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롱�ĺ���׳־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ب�������Я�˻ƺӳ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ű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й���ΰ..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и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롷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⺭����ʵ˿��û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롱�ĺ���׳־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ب�������Я�˻ƺӳ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ű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й���ΰ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ڡ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ϣ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ⲿ��ʮ���Եij�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֮־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и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롷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⺭����ʵ˿��û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롱�ĺ���׳־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ب�������Я�˻ƺӳ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ű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й���ΰ..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и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롷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⺭����ʵ˿��û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롱�ĺ���׳־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ب�������Я�˻ƺӳ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ű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й���ΰ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ڡ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ϣ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ⲿ��ʮ���Եij�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֮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ĵط��ԣ����Կ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ͻ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Ե֮�صĻ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š�Ѱ����ѧ���ġ����·��֡�����ô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֮�ص����ء��ӱ�Ե�����ģ��ɵط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д��ŷ��ĵġ�Ұ��Ұ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֮�У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ӵ����ǡ��衶ɽ����֮�ƣ���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µ�ȫ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٣���Ҳû�С��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ɱ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Ľ��ƣ��е�ֻ�ǡ����뼴�й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š�
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: ��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: 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: 2018-4
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һ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Ĵ��顣Ϊ�ˣ�����ɷá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С����飬Ҳ�����ջ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ҵ��زģ���ȴ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ν�����д��С˵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ͷ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ټ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ʨ��û�˰취���ֲ����뿪����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Щ��Ӭ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Ŀ�����ڣ�ȴ���Ժ��ʵ���ʽ��֮��£��ƪ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Щ�Բ�çç������ˮˮ������֮�һ���Զ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¥�Ρ��ȹŵ�С˵�¾�����Ч;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̹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Ĺ��²�û��̫�����⣬��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ᴩ�Ե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ʣ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˿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ع��Լ�һ���ļ�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ࡰ�ڱ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ɳ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ڸ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Ϊ���ĵ���ı��Ѫ�ȡ��ĵ��ı�����ɱ¾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Ļ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У�д����д���ţ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ڲ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棬�ƺ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ܡ��ο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ģ���ƽ��ԭ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졣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Ѩ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¡�С˵��չʾ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͡�Ұʷ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ʰ�˴�ǰ�ı�ī��С˵�ԡ�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ɼ�����ʷ��ԭ����ζ���ڴˣ��Կ�̽��ʷ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壬ȴҲ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90�������ʷ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ṩȫ�µ���ʷ��ѧ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֬��д�𡣲����룬���ˮ�ıӻ����飬��Ĺ�ı���ȴ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۲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⡱�ľ����㲻����ɫ�ط��˲ƣ��Ӵ˷ɻ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½���˸��Ƕ���λ����ע���ĸ���Ӣ�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���ڱ˴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ͭ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֤��Ҳ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ߡ�ͭ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ʷ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˵�У�ͭ�����ռ���ȴԶ����ʷ�ĵ�ʧ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ֻ��ռ��һ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̽�����ַ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⺭����ô��ʷ���ֵĿ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Ļ��ҡ�
����С˵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Ľ�ɫ��130�����ư���ÿ�չʦ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ϲ��֮�ʱ�ᴵ��߰ˣ�����̼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İ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Զ���ϵġ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Ҳ�߶ȳ����˼�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ʷ̬�ȡ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ϣ���ʳ�˼��̻�Ĵȱ���ȴֻ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ֱ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ij����У�ֻ�г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塣
�����ڡ�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ǿ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׳�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䴫˵����Ұʷ����֯�����ܴ��档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Ĺ��²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�ʷС˵����֮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ͼչ����ʷ��ԭ֮�еľ��أ�ȴ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ס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ʷ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ص��»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ơ��롰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ʷ����Ϊ���Ե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Ҫ�ķ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־�����붯��־�����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д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س�һ��д�����ݲݣ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ޣ�ȴ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ʯ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һ�ؼ�¼Щ��ľ����ô˵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־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Զ�Թۣ�����Ϊ��Զ��֤����ʷд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״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ô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ޣ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һ�����й��˵����£���ȫ���й��Ļ��ı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ڼ�ƽ����˵��ֻ�轫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Ϊ�й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Ϊ��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�ջ��㹻�ĺȲʡ�û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֮��̾����æ�������ʷ˼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ڡ�ɽ֮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ű����뿹������ʷǰ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س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Ҳ����ȥ���ĵ����⡣
������| ���
�ؼ��ʣ�

- ���·���
- �Ƽ�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+���ս�˹���ˡ��ٷ����ܡ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�20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è3���ϼһ�
- 01-30�°���̸���װ�˹�� ��ӰӦЧ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е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¿ƻ�Ƭ
- 01-30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˹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
- 01-30���Ҵ��Ժ���ں����Ϸ��̨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硶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 08-26���ݵ�ͼƬ��Ӱ��
- 04-29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Ϸ�ĵ���
- 12-17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 2019���⻪��ʫ�贺
- 02-19����
- 08-02���[��]
- 10-2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
- 02-11��һ�캣�⻪��ʫ�贺���ڶ���
- 04-232019���Ľ��мӹ��ʵ�Ӱ�ھ籾��
- 03-20��Ӱ[Ӣ]
- 06-26����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