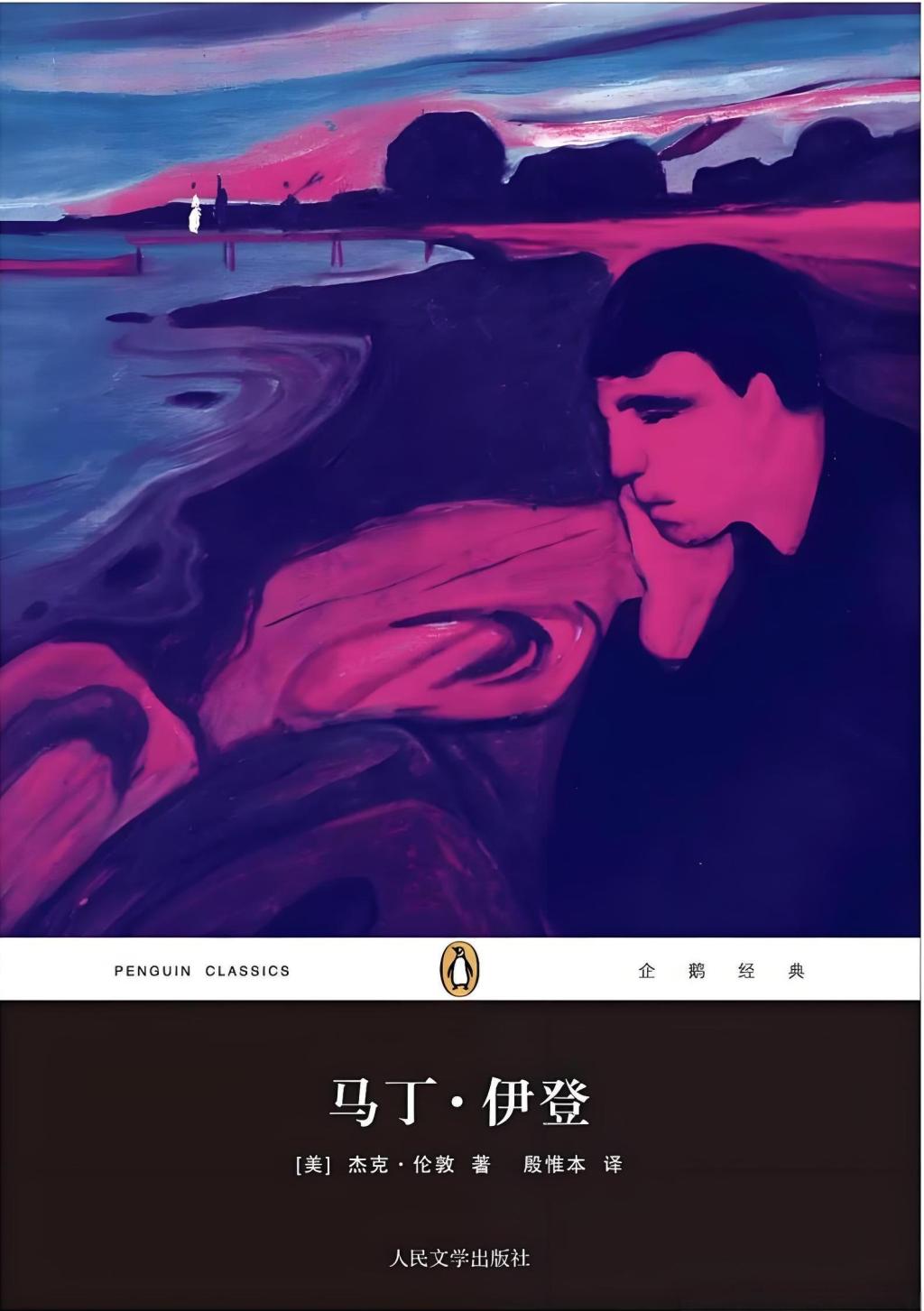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
����˹��һ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
ʱ�䣺2018-01-12 13:51:45 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 ��Դ��ͨ���ǿ� ������2017-12-22 ͨ���ǿ� WeChat ID Intro ͨ���ǻۣ��Ļ����裬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ᡣ ..2017-12-22ͨ���ǿ�
������2017-12-22 ͨ���ǿ� WeChat ID Intro ͨ���ǻۣ��Ļ����裬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ᡣ ..2017-12-22ͨ���ǿ�WeChat ID
Intro
ͨ���ǻۣ��Ļ����裬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ᡣ25��ǰ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IJ��ӱ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곤һЩ�ľ������ĵ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ʮ�塢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һ��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ѳ�һ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
���ò����ַ���ʲô�¼��أ�����9.13�¼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ã��䱦��ǰ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Ѫ���κ�һ����紵�ݶ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ո�ǹ����ˣ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ӣ���Ȼ��Ȼʹ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䵽�����ڿƣ�ͬ־�ǽӴ���ʱ��Ҫ���ɸ������衭����Ȼ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ڿ��Խ����õ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ǽ̵�Ա�����ǵĽ��ܡ�
���̵�Ա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Ӧ�ù��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ȥ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˹���еȸ��ӣ���ʮ�꣬��װ�����ر����࣬���е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ñ�һ˫����Ĵ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Ц�ؾ���ս���ǵ����⣬Ȼ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ǽ�ĵ����Ͽ�ʼ�μ�����ҽԺ�ڿƵĻ��顣
�Ӵˣ��ұ㿪ʼ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¡�
��ʱ½������Ժ�ľ�ҽ���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Ԯ��ʱ�ξ��ģ�ͨ����ҽѵ����ͳ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Ϊ26ҽԺ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Ψһ�ĵڶ���ҽ��ѧ���Ʊ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Ů����һ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糿�ܲ٣��ɲ��ǿ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μ�ϵ�����·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Ӳ飬˵�˾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ί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ٹ�·���ߵ��߹������Ƶ�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սʿ��ѧ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С�
�Ӵ��ö��ˣ�Ҳ��֪���Ķ��ˡ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ǴӸ�������½����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ǡ�9.13�¼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ɶ������밲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˹��Ϊ���չ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˵�̬��Ҳ��Ϊ�Ͱ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Ȼ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ڲ�ͬ�ĵط���ͬ���ľ�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⾫����ʱ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йء����ʡ��ĺ��壬������ذ��۹ⶢ�����Ľ��ϡ�70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Ь��һ����3507�����Ļƽ��Ь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̥�ĺ�ɫ��ͷ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Ь�϶�һ����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һ˫���ںڲ�Ь��һ˫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;����ر�Ư�����Ͳ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ջ����Ҵ�ͷ�����˲��ӹ��ڲ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ǰѽ��е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ܵ�47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磬һʱ�䣬����Ļ�ɫ������һɨ���⡣
�����26ҽԺ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ɫ�¼������ڿơ���ơ���Ⱦ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ӣ�Ժ���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ڿƵ�ѧϰ���ϣ��̵�Ա�̵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ʲ���˼��Ķ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ϰë��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ʲ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֤���Ͻ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ſ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ı�ĥ�µô�Ӳ����Į����ʱ���Dz����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˶��ڻ�����ȡ�뵳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Ծ;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һ�Ժ족�İ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ʹ�ļ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ظ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Ҳ�ھ����˹��˵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Ь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Ƶġ���̸���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ᡱ�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н��У��̵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̬����ս���Ƕ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𣿡�
��˹�����ͷ��
���Ǿ�̸̸�Լ��Ŀ����ɡ���
����ʱ��ֻ����㽲��һ�´�Ь�ĸо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ʱ���Ķ����и���ƤЬ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ƽ�ײ�Ь��Щ��ϰ�ߡ���û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е��ʲ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ؼ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˵�ú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ʲ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ʱ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ġ��Ҹ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
�̵�Ա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Ծʽ��˼ά�Ͳ���ɵļ��֣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⣺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㽲�÷dz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⿴���ܲ��ܻش���˵˵�������κ;��õĹ�ϵ����һ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+1=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ǵ�ʱ����IJ�֪�����̵�Ա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Ϸ���ԵĻش𣺡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еĻ�������
һ���µ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̵�Ա��ɽ���ˣ�ֻ�и�С�Ļ��̶ȣ�����ˬ��ʮ�ֿɰ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ָ�����Ǹ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紵��ս���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˭��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Ļ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ɼ�ͥ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ˮ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ѧϰ����ʮ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Ӵ��Ժ���ÿ����Сʱ���״���ѧϰ�У���˹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ǵĸ���Ա��ͬʱ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Ҳû�д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ࡣ���ң����Ǵνҷ��İû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
��˹����26ҽԺ����ʱ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
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Ӱ
70�������26ҽԺ���ڿƳ���ס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ţ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Ա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IJ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IJ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ֻ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¼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ԴӺ������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ϼ��ܾ���ÿ�춼��ҩˤ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죬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ˣ�һ�ij�̬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˶�Ц�ʺã�����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֮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��Źչ���ҽ���칫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Ѫѹ���β��ã��죡���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ˣ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ظ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Э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ҷ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ʳ���ô��°�ר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桱�����ҵ�ϴ�·�Ϊ��ר��ѡ��ŵIJ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ı�ҽ��ȡ����֮���ҩ����˺�Щά���ء�һ�����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ʹҴ�ȡ��ѹ�ڴ��ŵ����·���һ�ƴ��棬һק�½ǣ�����һ��ӡ�С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ֵĺ�ͷ�ļ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ˡ�
��˹��Ѹ�ٵؼ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ϵ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²�Ҫ���κ��˽�����
��ʵ���Ҹ���û�п�����ʲô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пᣬ�������ǵı������Ҹе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̹�ϵ�Ŀ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ͷ��
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Ժ�ˡ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ǰ��ͻȻ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۾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ȭͷ����С�һ�չ˺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
ֱ�����ڣ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Һ���˹��֮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ij��Ĭ����
��Ϊʡ����֦�����˵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͵����ݾ����Ļ�ѵ��ѧ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εĽ�ʦ������ҽԺ�Ļ�ʿ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Ϊ����ҽѧ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ݣ��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죬����ͬһ��ҽԺ��С��ͻȻ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ϵغ�ϸ����ս���Dz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սһ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Ƭ�̣���˹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ࡣ��
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ɱ��ϸ���ǵ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ϻ�ʤ����Ӧ�ø������Ǻ�ϸ�����ɱ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˹����ס�ˣ�����С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ǻ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Ц��
��ѵ�����ǰ��һ����ĩ���Һ�С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Ȼ��Ѫ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˹���ҡ�·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Ƴ��һ�ۣ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㡢��𪣬����һ���ϻ��۾���С��Ѹ�ٵط����Ҷ���˵�˾䣺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Ư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˹��ĸ�ף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Ӱ
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÷dz���ࡣ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ŷ��ŵ�ľ�䣬���ŷۺ�ɫ��ȷ��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ø߽��ձ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ע�ⲻ����˼��Ц�ˣ���Ϊ��ʱ���ӹ涨�κ��˲��ò廨��
��˹���ұ����˼��Ų��ɶ�õij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ᡷ������ԭ֮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Զ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ų�����ˣ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ر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Щ�ϣ����Dz��ã����Ƕ�ѧ�ᳪ�ˣ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°ûڲ��ѣ�����Ƴ�Ƭ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
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Ŷ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ź�һ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˴�Ĺ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ۼҵıʷ�ָ���ֱ��¼�֮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ϵĹ�Ȧ��ìͷֱָ�Ŵ��š��²��Ҧ��Ԫ����̧ͷȴ�ǡ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ͬ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Ⱥͱ�Ч������ҳϡ�
��ժ�·��ľ�ñ�������ؽ�Ļ�Ȧ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Ĺ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ÿÿ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Ѫ���ڡ����ǣ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ܡ�һ��һ��װ�ھ�װ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ʱ�����صذ�����ʫ�ݵ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ٿ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Ҵ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¸ҵ��ж��ˡ���ʱ����û���Լ���˼�룬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ְ�����۹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�ˣ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ھ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ò����װ����ڶ���ҹ�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12���ˣ���˹���ڻ�ʿ�칫�ҵ��ң��Ұ���ס���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š�
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𣿡����ʡ�
�����ҳ��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û�ȥ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Զ��Ҫ���ó����ñ��˿���Ҳ��Ҫ˵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Ҵ��ˡ��Ұ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δ�Ϲ�ս���ĺ�ƽʱ�����˵Ĺ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㲻֪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𣿡�
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ʲô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ѵ�ҡ�ֱ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Ҳ�֪���Ұ�һ�и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ȴ�ݸ���һ�⡶���Ľ��˴�Ĺ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ų�һ���亹����Ȼ�ܸ�����Ӱ�죬�ҶԵ�ʱ�й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⡰�ڴ����족����̹¶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
��С�����㻹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¸㲻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ܣ���ʱ�䣬���һЩ�顣�㿴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棬�Ͳ��ٶ�˵���ݸ���һ��С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ű��ġ���ʫѡ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10O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ܺ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ȴ�͵ÿ������ҵ�һ�ζ���ô�õ�ʫ����˵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Ͷ��й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�ľ���ȴֱ���Һ��ա�
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һ�γ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ô��Ļ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�ȡ�ϴ�ѧ�أ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ʶ���Ӳ�мһ�ˣ��й���һ����ũ��ѧԱ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괺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�ҽԺҲ��δ�Դ˱��ֳ�Ӧ�е�ɧ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뵳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Ͳ�����ѧ�ˡ���
�ҳԾ��ؿ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ĵ�·��
��Ҫ����ȡ��ѧ��֪ʶ���κ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õġ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Կ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£��Ҷ��Ȿ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Ϩ�ƺŴ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ֱ��ŵؿ�ʼ��֪ʶ�ĺ�����ѧ��Ӿʱ���̵�Ա���ڿ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ѱ���Ϊ��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Ҫ�ɵ�����ĵط�ȥ���±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ԵĿ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ղ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£�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ء���ͻȻ���ж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ο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ˡ��¼�����
�й��ڶ��칤ũ��ѧ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Ӣ�۳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ϼ���ָʾ��ҽԺ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ר��·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顣��Կ�ס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ͬʱ�ܽ��ѵĻ��С����ҡ��͡�ţ���̵�Ա�ԡ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ȫ�ƻ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һ�δε�ѧϰĥ�����ҵij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ƽ�ϣ��ҿ�ʼ�����Լ��ı�����ˣ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¾��ģ��㡢���Ʒ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Ȿ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ҵġ�
���ǣ�ֻ����һ�죬������˾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ǣ����а�ר��·�����С�ţ�Ļ��ϵ�һ�𣬸�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ѧϰ��һ�Ժ족�Ľ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ġ��Ŵ��ٿ�������֪Ҫ�㵽ʲôʱ��
˵Ҳ��֣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ɵ�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ݶ���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ר��·���ĵ��ͺ͡�ţ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ֹ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ϰ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ȴ�dz������ϵ�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һ�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�Ͱ�ȫ��
���ã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ȥ�˱�����
��˹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ڶ��꿪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Ѵ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ز�����С�ı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ע�⣬��Сƽ���ι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и��µ�˵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鲿�ȴ����䣬��˹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ҽԺ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֤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Ľ���һҹ֮�䱻�����ܻ���Ϊ�˶Ե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Ϊ�ҳ�һ����ڣ���Щ�˾Ͷ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뵳��Ҳ�����Žҷ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ʱ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ͦ���أ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̵�Ա�㼯��ս���Ƕ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ѧϰ���У����ֺ���ר����·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¿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塢�Ȱ�ͬ־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
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ӿ��һ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촽����ҧ�ţ����첻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̸̸�ɣ���˹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Ա֣�ص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ᄍ�м����˸С�
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Ľż⣬��ллͬ־�Ƕ��ҵİ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һ��࣬�����û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Ҫ��ôд���ر��ǡ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ԥ��Ƭ�̣�̧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û�к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в��ɷָ�Ĺ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ᶨ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Ϳ�����ԭ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
�᳡��ȸ������һʱ���Ҷ���֪��˵ʲô�ã���͵͵��Ƴ��һ�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⡢��Թ��ãȻ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У��ֺ���ʲô��û�С����ǽ̵�Ա�����˳�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֯�ῼ�ǵġ���
һ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ȥ���Ҹ���·�ϣ�˵����ʲôԭ��ֻ���ò��ij��ء��˵����˾���ô��֣���һʱ��һʱ���·�һ�ж������⡣ǰ���죬�һ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Ц��
�ߵ���ǰ����˹���ո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ˣ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ұ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
����֪���Ķ�ȡ��һ���ñ�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㲻�Ǻ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㡣��
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ҧ�����ܣ�ûͷû�Ե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˵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𣿡�
�����㣿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㵵�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ҵĶ�ͷ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ڷ��գ���
����û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飬�����ȥ��ô����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г����㡭����˵�ţ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৵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Ҫ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ôһ�仰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Ҫ˵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ˣ��㶵ؿ����ҡ���Ȼ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ҡ�ҵļ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ѽ���Ȿ�����ҳ�ϸ����ҵ�ӡ���أ���
�Ҷ�ʱɵ���ۣ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ٴεĹ�ʧ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ڣ��ұ�Ū�ÿ�Ц���á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ܶ�ɵ�£������Ϳ�ر��Ϻ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˻���Ҫ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ǵ��Ǿ仰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·���ñ���ȥ˵�ɡ���
��һ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˺ܾá�
��Ϩ�ƺ�֮ǰ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Ҿ�Ҫ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ѷ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Ũ�ص�ҹɫ�����ӿ��Ī������ꡣ�ദһ��࣬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˵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ȫ����·��ʣ�µ��ѱ�ùѵ���ζ��
�ؼ��ʣ�

- ���·���
- �Ƽ�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+���ս�˹���ˡ��ٷ����ܡ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�20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è3���ϼһ�
- 01-30�°���̸���װ�˹�� ��ӰӦЧ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е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¿ƻ�Ƭ
- 01-30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˹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
- 01-30���Ҵ��Ժ���ں����Ϸ��̨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硶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 08-26���ݵ�ͼƬ��Ӱ��
- 04-29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Ϸ�ĵ���
- 12-17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 2019���⻪��ʫ�贺
- 02-19����
- 08-02���[��]
- 10-2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
- 02-11��һ�캣�⻪��ʫ�贺���ڶ���
- 04-232019���Ľ��мӹ��ʵ�Ӱ�ھ籾��
- 03-20��Ӱ[Ӣ]
- 06-26����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