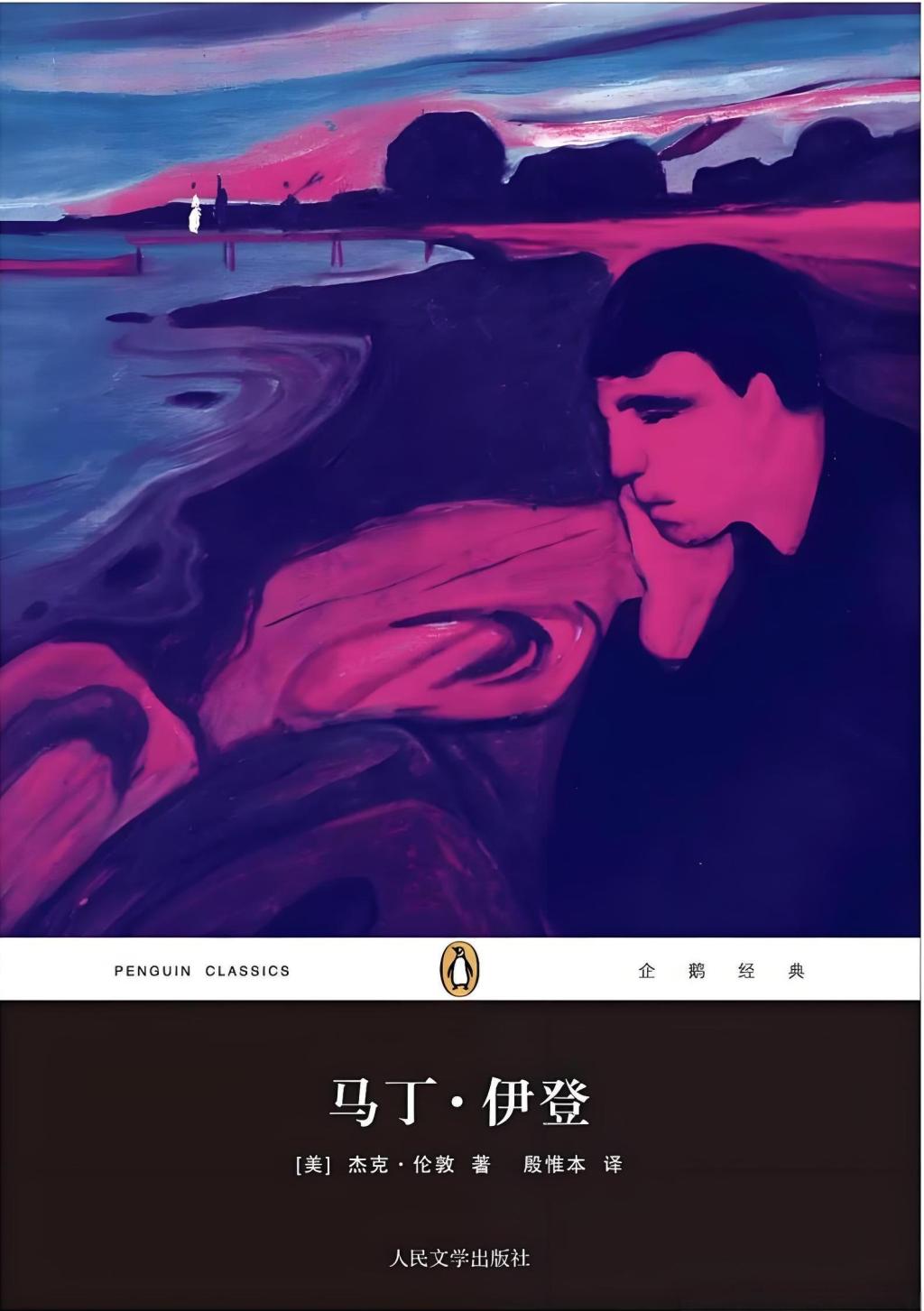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
���ξ�ح��ѧ�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ʱ�䣺2018-01-03 05:27:25 ���ߣ����ξ� 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ѧ ������2018-01-01 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ѧ WeChat ID hdsfdxwyxIntro 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ѧ��ʦ��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顢����רҵ��Ѷ�� ..2018-01-01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ѧ
������2018-01-01 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ѧ WeChat ID hdsfdxwyxIntro 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ѧ��ʦ��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顢����רҵ��Ѷ�� ..2018-01-01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ѧWeChat ID
hdsfdxwyxIntro
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ѧ��ʦ��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顢����רҵ��Ѷ����
��
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֮һ
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ںŵ�45�ڣ��Ƴ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ϵ���ξ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ѧ���ۡ�2017���3�ڵ����ġ���ѧ�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֮��ϵ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˵���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һ�ֶ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̻¶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һ�ֿ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䡰�ԡ������ɺͲ����ݵ��ص���ӽ��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ָ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д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͡���˵���ķ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ڹ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Խ�ڶ��˳���֮��Ĺ�ͬ�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е�һ�ֹ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ͬʱ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ֵ֮��ķ�Ұ�ҵ�һ���к�֮����
01
һ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˵
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˵�Ķ���Ҳ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߲������Եġ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ʴ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ǡ�Ϊ���ߡ��ģ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ߡ�ǡǡ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ѧ�ĸ���ּ�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һ�֡���˵����Le Dire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ֶ����ߵ�̻¶�ͱ��ף�����̻¶�ͱ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Һ��ޱ�����չ¶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ָ����ġ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˵�̻¶��Ϊ���˵ķ���ͬʱҲ����һ�ֺÿͣ����Դ˶�ӭ�����ߵĵ������ʹˣ�����ʵ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룬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̬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Ϊһ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䷢���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ϵ�̻¶��ʾ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֡���[1]����һ�ֲ����䱸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ֿɴ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ܽӽ��Ǹ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Ľ�չ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࣬Ҳ���ǹ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γɺ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ֱ�ӡ�����桱����һ��ֱ�۶������Ե�״̬�������ݻ�Ϊһ�����ԵĴ���ý�飬һ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ݺ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ݻ��Dz��ɿ��ܵģ���Ϊ���Ľ��ƺ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ڿ��ԡ���ʵ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Եȵ�������Ҫһ�������۵����ԣ�һ�ֿ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Ծͽ�����һ�֡���˵����Le Di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һ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˵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֪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յ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ǿ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κ������ڳ�Ϊһ�ֿ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һ�ֳ�����öɸ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͡��öɡ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ܱ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ʵ��ռ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ǽӽ�����֮�أ�Ҳ������֮�غ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֮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ȥѰ�ҡ���[2]
��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͡���˵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ศ��ɵģ�������ۻ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Ĺ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ܿ��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ʲô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Ϊһ��ֻΪ֪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ˣ����ܡ���˵���DZ���ģ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վ�ֻ����˵��һ�ֱ��죬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˵��Ҫ�ķ���ͱ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ַ���ͱ��ѱ���ȴ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Ľ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֮�ϣ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Ǿ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ԭ�����ܺ����Ρ���Ϊ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վͻ���һ�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ǿ���˵��ν���߸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壬���Ƕ��ڡ���˵���͡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һ��ֵ��һ�ֲ�ƫ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Լ�ֵ��Ȼ�����ֿ������Եļ�ֵ�ܿ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Ϳ�ѧ��ȫ�Ӷ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ߵĹػ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ܳ�Ϊһ��ѹ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ۣ����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̴�ͳ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̫�̵��ϵ۹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ĵ�һǰ�ᣬ���ڡ���˵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˵��һ��ʼ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ֻ�ܴ������ϵ�֮��ϵ�д��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еġ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Э�̵���Ҫ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ǿ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ϵ۴�֮���˵ġ�ʥ�ԡ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ݵ��ϵ�֮�ԣ������ϵ�֮�Բ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Դ����Ϊ��Դ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ィ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˵�ʹ������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롣��ˣ���˵��ָ�Ƶ��ǡ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ġ����ԡ�
ע��
����
[1][6]Emmanuel L��vinas. ��Paul Celan:De l����tre �� l��autre,�� Noms Propres. Montpellier: Fata Morgana, 1976, p. 52, pp. 49-50.
[2]����•��ά˹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83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6��档
��
1
02
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ѧ
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˵����ѧ���ŷdz����ܺ��ӵ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Ф�ͱ��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ġ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Ф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ۣ���һ�ְ�ʫ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ѧ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У���ѧ���Ե����彨������ϵ�ij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ӣ�����Ϊһ�ֿ�Ϊ��ͬ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ۡ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Ϸ������߶��ᴩ������֮ʼ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ǿ��Խ�����Ϊij�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Ф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˵��֮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ֿ����俹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һ�ֱ�ը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ı�ը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岻�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IJ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崦�ڲ�ͬ�IJ�Ρ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ʵ����ʹ�õľ���һ����ѧ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Ա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⡣�ʴˣ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ԾͿ��Գ�Ϊ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һ�����Ƶ�ȱ�ڣ���Ϊ��ʻ㲻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еĹ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һ�ֲ����߽����;䷨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ϰѴ��ﻹԭ�ɵ��µ��˶���
���ڲ���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۷dz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ȣ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Ϊ����Ф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⣬ȴ��Ϊ�κζ�����ʾ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ָ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˵���ʾ�⣬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3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ǿ���˵���Ѿ��ӽ��ڲ���̻�Ϊ����˵���ġ���˵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Ф�ⲿ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ⲿ�Ի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Խ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Фʫ�����Եij�Խ��̬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Ԫ�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IJ�ȷ���Զ����ɵġ���[4]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ȴ���ܽ���һ����ѧ�¼���Ҳ���ܽ���һ�ֶ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ҡ���Ҫ��Ϊһ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Ҫ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壬����Ҫ��ͬһ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ң�Moi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ʾ�⣬����ԵĽṹ����[5]���ң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Ϊ����Ф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ܳ�Ϊ����ѧ���Ե�ȷ�ϡ���ֻ����һ��ͬ��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Կ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ȴ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Ļ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Ҫһ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һ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롣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ά��˹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ij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ز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Եļ�����ƫ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̽����ѧ���Եı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ʽ���ػ�����һ�߽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Ե����۲�����һ�ɲ���ģ����˵�ڶ��ڲ���Фʫ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ά��˹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Ľӽ�֮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߶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ѧ���Ի���˵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ڶ��ڰ���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ҵ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ά��˹�Ѿ�Խ��Խ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һ����˵���ر���ʽ��
���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Ҫ��ʫѧ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һ���У���ʫ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ߵĶԻ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Ϊ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ʼ�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Ȧ����Σ�ա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IJ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ʫ�費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˳������߶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ֲ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̣�һ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Ϊ���ڲ�����ʫ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ű���Ϊһ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߳���һ�ֺ��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ʾ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Ҫ�ľ���һ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ʾ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һ�֡�û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 [6]��һ����˵��Ҳ���ǽ߾����ܵ�չ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ַ��š���[7]ʫ�е���˵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ϻ�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չ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˲��̻�Ϊһ�ַ��ź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һչʾ������չʾ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ʾ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Ϊ���ߡ��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ԣ����ֲ��ϵ�����չʾ��Ҳ���Dz��ϵ���ȥ���Ρ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ֲ��ϵ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ϵ����ɺ��˳����ҵ��ι̵�λ���Ӷ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λ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λ�ͷ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Ĺ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ubstitution����[8]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粻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Ĺ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ȴӭ����һ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ԵĶ��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λ�ã�position��Ϊ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ǿ��Գ�֮Ϊ���ң�Moi�������嶨���һ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[9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ͬʱ����һ�ֻع飬���ɴ�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ӵ�й̶�λ�õġ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˳�ԭ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Ĺ��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ɴ�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ϰ����չʾ�����Ź��̣�Ҳ�ͳ���һ�ֹ�ҡ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ڲ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Ϊ�ڲ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Ϊ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Ҳ��һ��ͨ�����ߵĻع飬ͨ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У�һ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ϵһ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˵�Ӧ��֮�أ���̫�˵����а
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˵֮��ϵ�����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Ӹ�Ϊ����IJ���ָ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ѧ֮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˵��Ϊһ���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ֲ�����֪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δ֪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һ���ڳ���һ�ֽṹ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֪֮�⡣[10]��ͬʱҲ��Խ�ڴ���֮�⣬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˵�û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ޡ��еĻ�����ô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ޣ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鲻���մ��ں���ʶ�İ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[11]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ֲ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̬�����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߸�˹֮�⣬�ų���Ϊ�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dz�Խ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֮�ϵģ���Ϊ��˵�����Ͳ��ܽ���һ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ʶ�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˵��˼��Ų�õ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д�С���ѧ�У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һ�ָ�Ϊ���ζ��¡��Ľ��Ӧ�����ܱ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˵֮���ԡ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ڵľ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ջ�����Ƚ��ѧ���ۼҿ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ٴη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˵�Ĺ�֮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մ��ں���ʶ�ľ���ų���Ϊ�Եģ���ѧ�Ļ�ɬ���Ѷ���ij�̶ֳ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ں���ʶ���Խ��ɺͺ�����[12]���Բ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Բų���Ϊ�ԡ�
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Ի���һ��ʱ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ʱ�ԣ�diachronie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ͨ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һ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롰�����ڴ��ڡ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־��벻���ڹ�ʱ��synchronie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ظ���м�����ij��ȣ����Ƕ���λ�ڲ�ͬ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ܶ���֮����ȷ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˵��һ��ʱ��ָ��һ�֡���Զ�Ĺ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ĵ�λ����һ��ȥ�Dz��ܱ����䣬Ҳ���ܱ��ݵġ���˵֮���Բ����ܱ�������壬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Դ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Ҳ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ı����Ķ���ͬ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ݵĹ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ͼ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ʷ�ʹ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ɵ���ʼ�㣬��һ�б����϶���һ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Ҫ�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ݵĹ�ȥ����ѧ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ͬʱ�䲻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б���Ϊ�ԡ�
��һ�����ݵĹ�ȥ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ı��е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Ҳ�����Ǵ�ͳ���Լ��ı��Եȵȣ����ܱ�����һ�ֵ�һ�����⡣Ҳ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ŵ��Ա����䲻�ɹ涨�ԣ�Ҳ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dz�˵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ѧ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Ҳ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һ���ڲ���Ф�ͱ����ص��˵���Ʒ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ı��е����ߡ���ˣ��ı��е����߾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Դ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Խ����Ϊ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ر�ǿ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Ĺ۵������ӵĻ�����һ�ı��е����߲�ֻ�ش���һ���ı��Ķ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ۺ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߲�ͬ�ĵط���֮���ı��е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Ѿ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˸����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ָ���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һ��ǿ���Ե����ꡪ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ѧ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Ҷ����Ǿ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ǿ���˵�ı��е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һ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ݼ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˿�ı����ߣ���˲���Ҫ�Ķ��߶���Ͷע�Ծ��ԵĹ��ĺ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ң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ȣ��Ȳ���̫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̫Զ����Ϊ̫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Ķ��߾ͻ����ձ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һ���ߣ�̫Զ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ˣ��Ķ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߽���һ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һ���棬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һ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룬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Ƿ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ϣ��Ƿ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Ĺ�ϵ���ı��е�����Ҳ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Զ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Խ��Խ���Կ�Խ�ļ�ࡣ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[13]
ע��
����
[3][4][5]Emmanuel L��vinas. Sur Maurice Blanchot, Montpellier: Fata Morgana, 1975, p.39, p.78, p.39.
[7][13]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ϵ�•������ʱ�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235ҳ����234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顤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1997��档
[8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Ϊ��Ҫ�ĸ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λ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Dz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��³�Ϊ���˵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ɾ������壬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Ϊ���˸����е��ң����Ƕ�һ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ҷ·����Ǹ�Ψһ�ı���ѡ�ߡ�
[9]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ϵ�•������ʱ�䡷����221ҳ�����ĸ��ݷ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иĶ���
[10][11][14][16][18]Emmanuel L��vinas. Autrement qu����tre ou au-del�� de l��essence. The Hague: Martinus Nijoff Publishers, 1978, p.241,p.240, p.241, p.246, p.242.
[12]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ȿ����ڲ���Ф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Ϊһ�֣��뺣�¸��ʽ�Ĵ���֮����Եģ���ҹ�Ķ�λ�У�Ҳ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�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εĹ����У��ҵ�����֧�֡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İ�����ȶ��ֳ�ν��
��
1
����Ŧ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ᷨ����ѧ�ң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28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ѧ��
Ԫ����ʲô��
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Ȼ��Ҫ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ģ����Ķ��У�Ҫ�ӽ��ı��е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ʹ�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˵��ѧ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ʽ�Ļ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ı����Ķ�ȴ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רҵ���רҵ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еĻ��ձ黯�Ĺ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ijһ���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ʶ��ϵ�У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ѧҲ�ʹ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ܵģ���˵Ҳ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˵�Ĵ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з��ӳ��乫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Ķ���ʽȴû�й˼���˵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һ�ֱ����ķ�ʽ���鲢�������еĻ���ϵͳ֮�С�Ҳ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DzųƵ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еĶ��ߣ���Щ�ܼ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߽���ѧ֮�е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ߣ��Ȿ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Ķ��߱���Ϊ��ŵĶ��ߣ���Ȼ��Ҫ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ѵģ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ϼ��ѣ���һ�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߾ͳ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ˣ����ǿ��Խ����ּ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飬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Խ���˵����ѧ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⣬ת��Ϊ��˵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һ����Ĺؼ��ǡ���ͨ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ֲ����ٲ��죿�� [14]��һ����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Ⱥ��ִ��Ķ����۲�ͬ���ǣ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ᳫһζ�����Ķ��б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ɲ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ܹ�ͨ�ܿ��ܻ�Ĩɷ���죬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ͬһ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ֲ���Ҳ�DZ�Ҫ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Թ�ͨ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Ҫ�ڹ�ͨ�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IJ��졣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�����ѧ��˼��ͬ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Ĺ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Ĺ�ϵ���Դˣ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й�ר�ŵ����ۡ��ڡ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һ���У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һ�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ԵĹ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У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룬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ϧҪ���ø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Ҳ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⣬Ҳ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ģ��ʴ����ſ��Դ���˼�롣
����֮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һ���۶ϣ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Ӧֻ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̬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Դ�ʥ���̬���ǿ��Դ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Щ�ı�Ҳ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Ϻ�ǫ����̬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⣬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бȽϣ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Ҫ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˿��ģ����ڿ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縺��һ�ֹ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繫���ش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
���˵���ߵ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ߵ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ı����н鹹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ҡ��㡱�Ի�ģʽ�Ļ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д��һ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һ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ߣ�Ҳ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ʼ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-����-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ɵĹ�ͬ�壬���ǿ��Խ����ֽ���ģʽ��Ϊ����-��-����ģʽ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᱾���϶��ǡ���-��-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չ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һ�ֹ������Ρ�[15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й����Ե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еĽ�ɫ�ܽ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le tiers����
�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ͨ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Գ����빫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֮�Խӡ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Բ��Գ��Ե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һ��Ψһ�����߶��ԣ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ġ�Ϊ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ѯ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Ҿ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縺���Ե����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ߵĵ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˵�Ҵ�ʱ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һȺ���ߣ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Ҳ�Ͳ�����ֻ�Ǽر���һ�ֲ��ԳƵ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ߣ��һ���Ҫ����Щ���߽��бȽϣ��Ӷ�ƽ�ȵضԴ����ǣ��һ���Ҫ�ڹ᳹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ԭ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ֹ���ͺ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Ч��ִ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ֱȽϺͺ����漰�ľ��ǹ�����ƽ�ȵ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ĵ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ݣ��ȿɱȽ��ֲ��ɱȽϣ�һ�Ŷ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ڹ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б�ÿɼ�����[16]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Ŵ�ͳ�����Ϊ�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Ҳ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ѧ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Ρ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β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۵��ص㣬���ܶ��ڹ����ռ��̽����Ȼ�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��ǹ�ע�Ľ��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߶Ի���ʱ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ߣ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˼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һ�����ѧ��д��Ե���һȺ�����Ķ��ߣ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۸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һ�ֶԻ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۶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֮��ĸ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д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֮������жϵ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ݽ��бȽϡ��ۺϡ����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ļ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߽��бȽϺͺ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ķ�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߽��бȽϺ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ܻ�Ϊ��ͥ����ͥ���ǶԹ������вöϵĵط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е���Ҳ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ڷ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ͬʱ�е��˷��ٺ���ʦ�Ľ�ɫ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ͬʱ��ҪΪ��Щ���н��н��ͺͱ绤��ͬʱӵ����ʦ�ͷ�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ն���Ʒ���н��ͺͲöϵĴ�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д���ջ������ռ䣬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кͼ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ʽ���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ռ������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Ϸ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һ�֡�Ϊ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ı�¶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ǿ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-���߹�ͬ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ռ��ͬ���и��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[17]��Ϊ����ѧ�ҿ��Խ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֮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һ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ϣ���Ҳ��û���κβ���֮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߸��ӳ���س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Ӷ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ζ��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ʡ�
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ߺͶ���֮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ֻ�ܳ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ɫ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ֱذܵij��ԡ����˵��ѧ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˵�Ļ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빫������Թ��ڷ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뻯�����ⶼ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Եģ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ԣ���ע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ˮ�����°㲻���ܵģ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˵��Ҳע����Ҫ�ܵ���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νһ�ֱذܵij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ذܵ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ij����ʹ�Ҳ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ζ��Ȼ���Ⲣ��ֵ�ñ������෴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Ϊһ�ֳ������廯�Ļ������Զ�ᱻ��ܣ�Ҳ����Ϊ�ᱻ��ܣ���Ҳ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Ĺ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⻯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˵��d��dire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ֲ��ɱ�ͬ���IJ��죬��ָʾ��Ϊ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ߡ�[18]�� 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˵���Ĺ����У��ܱ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˵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˵ͨ���Լ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IJ���˵����˵ͨ������֮˵����ʾ��˵��ͬʱҲ�ڸ���˵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Ա���Ϊ��˵�����෴����˵Ҳͨ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˵�Ĺ�ϵ������Ҳ�Ͳ�����һ�־������廯�Ļ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ϵҲĪ����ˣ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ʾ��ѧ�е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̼�����Ҫ˵����ѧ�е�����֮�⣬Ȼ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ѧ��֤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Ʒ���ף����䱣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֮�¡�Ҳ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ּ����ø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ѧ��֮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֮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ǡ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Ҫ�˷��ͳ�Խ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̽����䡰Ϊ���ߵġ���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Ӷ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µ���ѧ����ģʽ��[19]
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ģ��ϵ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ϣ�һ�粼��Ф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벼��Ф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ȣ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ȣ������Ŀɴ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Ĺ����ռ䡣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ռ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¿�ʼ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չʾ��˵��ֻ�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빫���ռ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Ӯ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ѧ���ı��Ķ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ƽ�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֡�Ϊ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ȡ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ӽ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֡�Ϊ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��ݸ������ռ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һ�ռ��У�ÿһ�����߶��Ƕ�һ�ģ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Ҳ��ֻ���ҡ�Ϊ���ߡ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Ҳ�ǡ�Ϊ���ߡ��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У�һ�ָ����ܺ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ռ俪ʼ���ɣ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ھ���ÿһ���Ķ��ߵĴ��ݹ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Եĵ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ޡ�����IJ��͵�Ȼ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а�룬���а����屾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۵�ɫ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ζ��ÿ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[20]
�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ռ�֮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һ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Ծ�Ϊ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Ӧ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Ϊ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ͨ��֮�ϣ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Ķ����ֿ��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ľ�½⾭��ͳһ������Щͨ���Ķ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ı������ϵIJ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ʶˣ����Ǿ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д�ߡ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ǣ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-��-�������˽ṹ������һ�ֽ�ɫ�Ļ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ߣ�Ҳ�Ƕ��ߣ����ߺͶ�����ȻҲ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Ĩ�������ߺͶ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ݲ�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߹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ܵĹ�ͬ�壬�����У�û��˭���ھ��Ե�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ۺ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ּ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г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ֿɽ����ͻ����Ĺ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ɵ���ҪĿ�ꡣ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٣�Ϊ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IJ��Գ��Ժ�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ߵ�ʱ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�߱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Ϊ�ؼ��ĵط����ڣ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Ĺ�ϵ�У����ұ���Ҳ���Գ�Ϊ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ߺ͵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ʱ�����Լ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ߺ͵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ߺ͵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ϵ��Ťת����ά��˹˵Ψ�С�����л�ϵ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Եĸ�ծ�ߣ���û��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ģ�Ҳû�а취�����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Ĺ�ϵ�����ϵ۵Ķ������ҳ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ֽ����ԣ��ϵۿ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Ĺ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ϵ۲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ĶԻ��ߣ��ϵ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[21]
ע��
����
[15]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-�㡱ģ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롰��-�㡱֮������ܶԻ���ȣ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ǿ�����߲��ɰ��յļ��ˡ����ԡ���
[17]̨��ѧ�ߵ�Ԫξ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ѧ�е��ı��ۡ�һ�Ķ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࣬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Ĺ�ϵ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Ϊ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˵�����Դˣ����ֲ߳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λ���Ӷ�ӭ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߳�Ϊ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˵�Ľ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ߣ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һ�Ĺ۵����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һ�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Ĩɱ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ԣ�ͬʱҲĨɱ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ң��ֺ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ߵij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Ĺ�ϵ��Ҫ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ĸ���ռ�����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ų�Ϊ���ߵ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ζ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ѣ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֮�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̻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ȥ��˵֮�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ͱذܵ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ǿ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(�����ϵ�)����˵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ϵģ�����˵��֮�ˡ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Ϊ��˫�ص����ʡ��ε�Ԫξ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ѧ�е��ı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183ҳ��2007���4�ڡ�
[19][25]Emmanuel L��vinas. ��La R��alit�� et Son Ombre,�� Les impr��vus de l��histoire. Montpellier: Fata Morgana, 1994, pp.124-126, p.108.
[20]Emmanuel L��vinas. Difficile libert��, Paris: Albin Michel, 1976, p.139.
[21]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Կ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λһ�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Jean-Luc Mario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һ�塱��һ�����Ĺ�ͬ�壬�����ͬ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ٱ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ͬ�壬����һ��ͬ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һ�ֲ��ԳƵĹ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Ӷ���ÿ���˶��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ݣ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̲�˵��ά��˹˽�³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һ�ְ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Ӷ�ʹ�����ߵĹػ����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ࡶ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3������40-41ҳ��ͬ�ô�ѧ������2008��档��
��
1
04
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֮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֮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̡�һ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Ķ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1800��ǰ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һ��ּ�ڽ������ڽ̺͵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ȹ۲죬�����ѧ��ֻҪ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ĸ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ִ��ɵIJ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忪ʼ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˼�Ͷ�����ʽ�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Ϊ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ڣ��ڷǵ��µġ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˶��ĵġ���ª�ġ���̬�ĺͲ�̬�Ŀռ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Ϊֹ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Ϥ�ģ����߿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ķɵء���[22]����һ��ѧ�У�����ѧ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ý����õذѶ�����ѧ�Ķ���[23]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⺭��һ���Ƿǵ��£�һ���Ƿ����£��ǵ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塢Ψ�����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Ĺ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롣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ǵĴ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¾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γ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Ҳ��˳�����µ��Ƴ��˶����ѧ�ĵڶ����⺭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ѧ���ǿ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µĶ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ö����ѧѹ���˵��¡�
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Ϊ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ֻ��һ�ֱ��ֶ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ѧ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㣬��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£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뱾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䱾����Ҳֻ�����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ȣ�ǡǡ�ǡ�Ϊ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Եġ���Ҳ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̬�ȣ��ڡ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Ϊ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߸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Ǿ��Ƕ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һ�֡����ԡ���װ������ν�ġ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ϣ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һ��ѧ�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Ψ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���ﱾ�����еġ�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Ծͱ����һ�ַǵ��¡����ַǵ����ںܶ���ѧ�Һ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һ�֡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Ѿ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ַǵ��º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ջ��ݻ�Ϊ��һ�֡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ķ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˵���ף����չ黹��վ���˵��µķ��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º���ά���ϵ�ȱʧ����ͨ��һ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�[24]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̷����з�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뾭�ѵ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�ѧʷ�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ǿ��Է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ڶԴ�ǰ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з�չ�ģ��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Ҳ�ܸ����еظ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ѧ�Ľ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塢����ʵ���塢��ʶ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ַ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һ�δ���ѧ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컹��һ�ּ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ġ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�����ֲ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ֵ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õĽ��ڣ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ͬʱ�������㻯�;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˥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Ļ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Ѱ��һ���µ���˼·�������ֺ��ִ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Ԫ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Ϊ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ܱ�֤�䲻��Խ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ʧ��Ҳ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ǿ�ҳ����
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ҵ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Ҫ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㣬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е��Ž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 �����Σ�[25]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Ͼ�ͨ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ҵ���һ���к�֮����ǰ���Ѿ�˵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ʵ���ге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ٵ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жϵ������١�judg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judgement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ͬ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һְ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Ȼ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ֻ��һ���侲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йٽ�ɫ���෴�����Ƕ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һ���Ĺ����Ͷ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ġ������Ͷ�뱾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ң�֮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Ʒ�ʣ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Ͷ��ͽ��䲢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ij��Ը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DZ�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Ϊ�����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߶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Ϊ����ȥ���ѣ�ȥ�����ԡ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ֱ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Ļް�֮�ء�
Ϊ�˸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,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߶ȷ�չ�����ͣ����ζ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ѧһ����ﵽ�˼��ߵ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ٹ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еĵ��½��漸����Ȼ�棬�е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״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ν���ѧ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Ҫ���⡣
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 ��֪�ԡ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ѧ�͵��¡�[26]��ν��֪�ԣ�intelligen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ǣ���ȷ��˵����ָ��һ�����Ե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ʴ���̸�۰�ŵ��ʱ�����ᵽһ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Ա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жϵ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ľ������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27]Ȼ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Լ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ԵĻ�����ô�ִ���ѧǡǡ�Ƿ�֪�Ե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˵�ģ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ɿ϶����볣ʶ���ɵ����磬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൱�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Ժ͵��µ����죬�ִ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ص�ǡǡ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֮��Ϊ���䡱��[28]��ˣ�֪�Կ϶���ֻ��һ�ּ����ԣ�Ҳ����һ�ּĵ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�µ���ѧ��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أ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˵���ְ��ȫ�鶼�ڶ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Ĵ𰸡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һ���棬����˹�Ƕ�ʮ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ѧ��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ڶࡰ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ӡ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ϣ��Dz����ܵõ����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㯺Ͳ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˹Ҳ�Ǹ���Ϊ���Źֵ�֮�ˣ���ʹ�ڸ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Ҳ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ѩ���β��ų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𣿡�[29]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̬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һ�ֿ��ݵĽ��ͣ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ռ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꣬ͬʱ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ķ�ʽ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볬Խ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ԣ���ʵ�̶ֳ���Ϊȫ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ʵҲ���ڶ��ִ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һ���ҵ����ж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źεȺ��˵�Ұ�ޣ����Ǿ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�˷ܸС���ס���й��ҵ�֪ʶ�ܶ����dz�Ϊ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ṩʵ���Ե��洦����[30]��Ȼ�����ɷ��ϵ��ǣ��ִ���ѧ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Ե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ķ��գ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ɵ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Եľ��硱��[31]���ҵ��ǣ����ܳ����ջ�����˹ȴû�п����Σ�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а���Щ����Ļ���Ӹ�С˵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ʥͽ���˹�ٷ�•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ﲼ³ķ���ϣ���ͱ�ס��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[32]
���ˣ�֪�Ե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ְ�𡣶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λ��ҲһĿ��Ȼ��֪���˵���ְ֮����ѧ��֪��ְ֮�����ֹ��ɣ��ȱ�ȫ����ѧ�Ĺ����ԣ�Ҳά������ѧ�Ķ����ԡ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֮��Ĺ��ɺ��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Ҳ��֪���ڷ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£�֮����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Ҫ�ı����ߺ�ִ���ߣ���Ϊ���߲���ֱ�ӳ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Ʒ�Ĺ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һ��֪�Ե��ӽǷ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һ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һ�ֵ��¹涨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ָ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ѧ��ͨ����˼�Ե��ж���Ѱ�ٵ����¼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̺ʹ�ͳ���ټ������ַ�˼�Ե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ж���Ϊ�н�����ͨ��ͬ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ֿ�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Щ�õ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ȴû����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̬�ȣ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һ��ͬ���̬�Ⱥ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ŵ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ڳ�ֽ����ı�ϸ���Ϳ���Ļ����ϣ�ͨ���Լ�Ԩ����ѧʶ����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λ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ͳ�С�����¾���һ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ڴ��ĵ䷶ʽ������[33]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Ȱ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ߣ�Ҳ�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統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ڶ���֮�仳��һ�֡�Ϊ���ߡ���̬�ȶ�����ͱ�֯��
ע��
����
[22][23]�˵�-������•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ǰ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 ���룬��2ҳ����3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14��档
[24]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Ҫע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ͬ�ĸ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ġ�Ԫ����ѧ���ֲ�ͬ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
[26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Щ�۵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¾�������2011-11-19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Ϊ����ѧ��֪��ְ�𡷡�
[27][28][29][30][31][32]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֪���˵���ְ�𡷣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ĭ�룬��392ҳ����394ҳ����475ҳ����401ҳ����478ҳ����478ҳ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2011��档
[33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̫�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̫��ͳ�Ļ����Ÿ��ӵ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Ƕ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ѧ�е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Ƚ��о���
��
1
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ξ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ˣ���ѧ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ϵ˶ʿ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ô�Ӣ�����ױ��Ǵ�ѧά��ѧԺ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Ҫ�о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̫-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ѧ˼�롣�ڡ���ѧ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: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й��Ƚ���ѧ���ȿ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ƪ�����桶�屾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ά��˹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⣺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ά��˹�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
�ؼ��ʣ�

- ���·���
- �Ƽ�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+���ս�˹���ˡ��ٷ����ܡ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�20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è3���ϼһ�
- 01-30�°���̸���װ�˹�� ��ӰӦЧ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е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¿ƻ�Ƭ
- 01-30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˹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
- 01-30���Ҵ��Ժ���ں����Ϸ��̨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硶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 08-26���ݵ�ͼƬ��Ӱ��
- 04-29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Ϸ�ĵ���
- 12-17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 2019���⻪��ʫ�贺
- 02-19����
- 08-02���[��]
- 10-2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
- 02-11��һ�캣�⻪��ʫ�贺���ڶ���
- 04-232019���Ľ��мӹ��ʵ�Ӱ�ھ籾��
- 03-20��Ӱ[Ӣ]
- 06-26����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