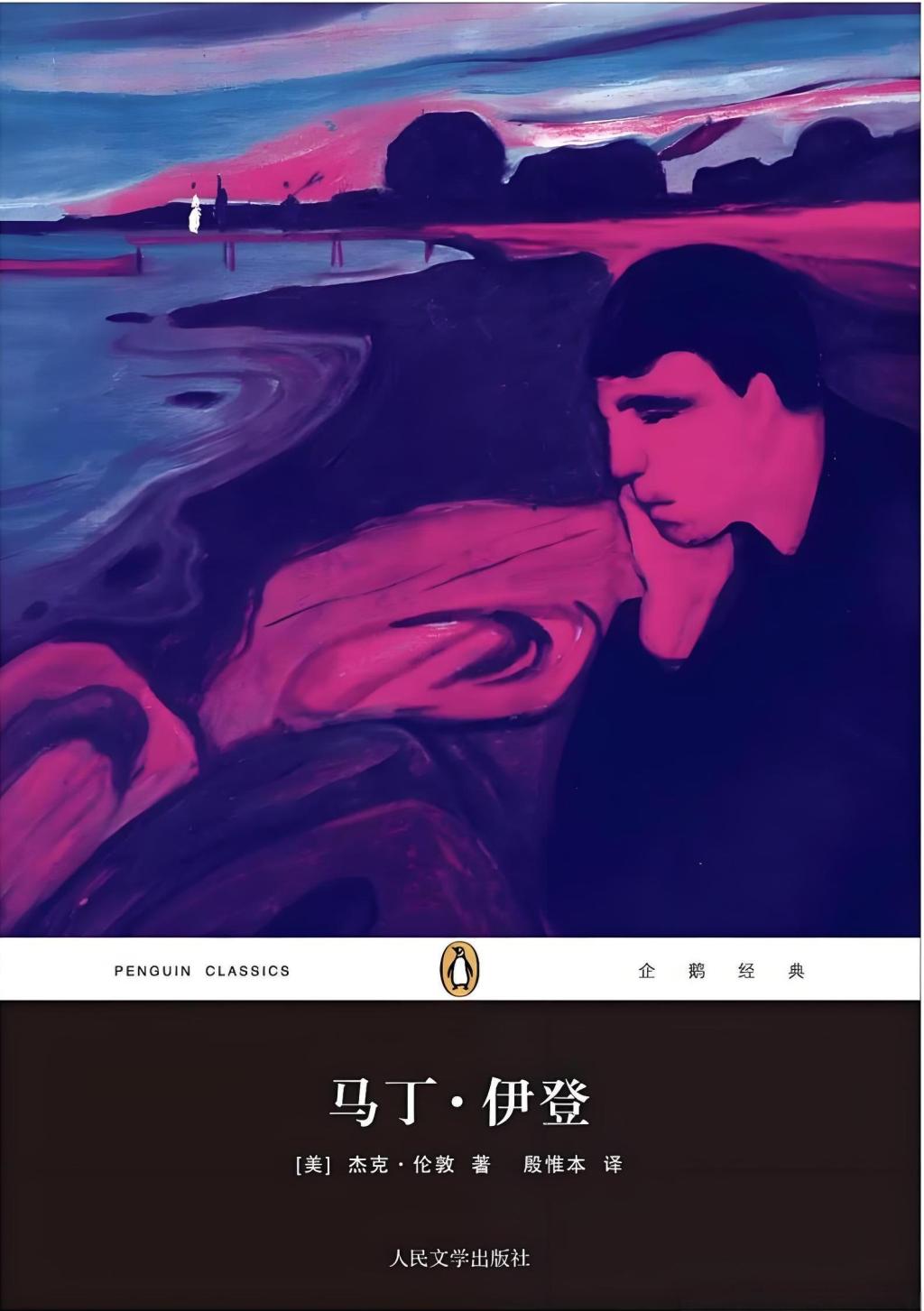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
������ 2015-05-12 05:17:49����Դ: �����ձ�(����) 0����IC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γ� �㡡 �����ʳǸ��³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ʿ�У�����סͨ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·�ߵ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ϴ��˼����̵Ĵ��¡�ԶԶ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Ƭ�ȵض���ĸ�..2015-05-12 05:17:49����Դ: �����ձ�(����)
 ����IC��ͼ
����IC��ͼ 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γ� 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γ� ��
��
�����ʳǸ��³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ʿ�У�����סͨ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·�ߵ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ϴ��˼����̵Ĵ��¡�ԶԶ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Ƭ�ȵض���ĸ��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ְ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Ǹ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ⲻ�����ǾͲ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��һ�֣�ŨŨ�İ���ü��̸��䣬ԲԲ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ź��ӵ����շ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С��һ���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·��һ�ڶ��Ǿ�ǻ���ص�Բ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ס��ôԶ�أ��� ���̲�ס�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Ͱ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Ц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һ���Ժ��ͬ��˵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Ա��Ե��Ļ��硶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ž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ݣ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ס�ˣ�û����Ʊ�ݸ�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һ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ѩ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Ӣ��ûʲô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ôһ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¸ң����˶��۵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Ϊ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00�˺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ϣ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µĽ���Խ��ת�����⻯����ʱ�䳤�ˣ��ͻό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٣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һ�ߣ�����֢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
����Ц�ö����ۣ�һ��ĥ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д�ı���ģ�²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ִ���Ϸ��ʷ�ϣ�����ʿ�д�Լ�Ǹ��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 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֮�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̨Ҳӭ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б���ɫ�ʵ��ִ�����Ʒ��ʼ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Զ�ġ������źš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Ϻ�ң���Ӧ�ġ��췿�䡢���䡢�ڷ��䡷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й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ȫ�¸о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е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³嶯�ķ�Χ�£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Ԣ���Ե�ɫ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9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�
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1993�����ݵġ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ڻ�����Ϊ�Ժ��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Ʊ���˴����糡�ſ��ų�һ���أ���ӿ�����Աߵı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ɽ�˺���һƱ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ͬ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ֻ��1979�����յ�һ�θ��š���ݡ�ʱ���ֹ����˺��δˢ�£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𱬾��ǵġ�ϲ������ˡ�Ҳû�ܴ��ơ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µ��ŶӼ�¼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ʿ�е��ı�����һ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Ĭ�ͻ����̨�ʣ���ײ������Ԫ�أ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ṹ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ڣ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ˡ���ͳϷ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ǰһ����һʱ�䣬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ˣ���ʿ��Ҳ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����ų��˴��ֱʵ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
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ˡ�Ҳ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糱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ﶼ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ʮ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ʿ�е���Ʒ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Ȼ��˵�Dz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С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硱���Դˣ���ʿ��Ҳ����ΪȻ������һЦ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дһ��Сʱ�������硣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Ҳ�д����д���ı���Ҳģ�²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6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ġ����ˡ���ΪԺ�ؾ����ٴ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հ�����̨��ϷƱ�����۹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ɫ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硱���ܷ���Ҳ��Ϊ���κ��ɱ�ľ籾��ֻ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ԵĻ�������Ĭ��һ�����Ǵﲻ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dz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ʿ�е�Ϸ����Ȼ�dz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ү��æ�ڰ��ֶ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ҹ�ͬ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Ƕ���üȴЦ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ѱ��ʿ�С�
����1952�궬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꣬��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Χ����ұ���Ǩ��Ҳ�����꣬�漮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游������ΪΧ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ϱ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붨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һ��Χ����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硣
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Ũ�صġ����ˡ�ӡ�ǡ����֡���ʿ�С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桢��ĩΧ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Ĵ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ѱ��ʿ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˵ĺ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ڹ�ʿ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У��游�����游�������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֣�����ָ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壬����Χ���ӵ�ʱ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ױȡ�����˫�ֺ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硶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
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ˡ���Ѫ���ɹ�ʿ��û�ܰ����游����Ը��Ϊһ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Ϊ�Լ���С�Ͳ��ó���һ����ѧ�йص��£��侭���깬���游�ĵ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ξ��Ȼ��ֹ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첻֪��˭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ͭ������棬�Ҿ�ÿ��ߺ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ŷ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�ڳ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Ҿ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߱���Ȼ���ˡ����ٴ�һ�㣬���ְ�������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ڼ��ϣ�Ȩ�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ˮҨ�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ɿ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쵽��û�ܳ�ȫ����Ϊ��ʱ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ʶ�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˵���Ӵ����Ρ�Сѧ���꼶���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ֺ�ѩ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һ�ο���ƪ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3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˵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£���һ���ߴ�ֺڵ�ɽ������Һ�ʧ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Ŷ�С˵������㽣���ʿ�п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һ�ֿ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һ��Ǯ�������վ���죬���˲�ע��ʱ͵͵���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ܿ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ơ���˵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컷�ε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⣬���崫�棬ȫ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�Сѧʱ��һ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˹�ġ���ͥ��˽���ƺ��ҵ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𣬾�վ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Ų�˼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̥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ķ��ѽ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�ý����ζʱ��һ�����ݸ߸ߡ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깤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ܺ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飿���ĸ�ѧУ�ģ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ܷ�ŭ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֮زز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ο�塣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ʲô���Ա�ȫ�Ļ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˲�С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ʹ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֮�С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�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ү�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ո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㡣
������Ĭ��ڶг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ӡ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ң�Ц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ʰ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ĸ����æ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С�š�����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ɥ�ӵ���̫̫������Ψһ�İ��þ�������ϻ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�յ�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Ѭ�ա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ݴ������³����ô�ڽ��ĵ�С�����ŵö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µغȾơ�����ʿ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塷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ϸ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ȺӢ�ᡷ�����ɵ��ݷ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쵽���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���Ƶĵ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顣һ����ɮ���˽䣬����ɳɮ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δ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д���˺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Ĵʣ�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ִ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
������Сʱ��ƽ���и���Ϸ���ģ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վ�ţ��Ŷ���ľ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dz�ƶ���Ҷ�Ҫ���ˣ�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ͷ��ʮ�ߣ�Ȣ�����Ű�ʮ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Ӿ�ʮ�ţ��ø�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Ϸ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δ�ȴ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СС�ӵ��Ժ��С�
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ͷ���˵Ĺ�ڣ�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к�����Ķ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Լ�ǿ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ģ��ö���֮����ʿ��Ҳ�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Сѧʱ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Ů����Ϊ���Լ����ߴ��ڸУ��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潲������ŵĸ�ҥ�������治�Դף��ڴ���ʲ�⡱�������治��±���ڴ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治��֭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治���Σ��ڴ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ǹ�ʿ�е�ͬѧ��Ϊ�˸��Ƕ��İ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ڴ����²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ĸ�ҥ33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֡��У�Ҳ��֪�ж���ϣ����Ϊ��ѧ�ҵ�ͬѧ�������ҵĸ��Ŷ�����һ��
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û���ϵ����ǣ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ֿ��ʰ������Ը�Ϊ���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21��ʱ����ʿ�м�û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û����д��֮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ת�˸��䡣�Ӵˣ�����ʼѧ������Ĭ�Կ�ѹ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ӷ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Ϊ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�ֲ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ʿ��ʼ�ա����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θ��Ѳ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䲻��ΪȻ��ȴҲ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˲ܲ���̤����Ĺ��£����մӶ������Ѻͻ�ϻ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𱬾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Ȳ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�ͻ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ٰܲγ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ݲܲٵĽ���ɱ�˲���Ѫ��Ѫ��մ���зƱ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ʿ��һ��˵�˰��Сʱ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֯ȫ��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Сʱ���ҿ���һ���²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ʿ�У��Ǻ��Ƕ�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㶮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ײ㣬��һֻ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Ͳ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沨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һ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˵�⻰ʱ�������dzϿҵ���ɫ��
����ʵ���ϣ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˼���ת�䡣
����1978���һ�죬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ȥϴ�裬�Ӵ̴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ѧԱ�����Ϣ��ͬ��Ȱ��ȥ���ԣ���Ҳ��Щ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ҽ���ֱ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硣��
�����Ǵο���û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ھ�26�����ջ��м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¼ȡ֪ͨ�����ǣ��ٴο�����Լ�ȥ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̡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ҿ졣��ҵ���˹�ʿ����Ϊ�ɼ����㣬���ձ����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Ϸ�����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ֶ��˵�Ϸ�����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Ϊ��һ�dz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һ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ʿ�ж������ھ糡�ͺ�̨������Ա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�15���У����˼�ʮ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ǧ��Ϸ�����Ҳɷù��ϰ�λ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ѬȾ�͵㲦���ù�ʿ�е�����ϸ��ïʢ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嶯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ζ��Ͷ���ϴ�翪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Ϸ����д�ɣ�ֻҪ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ܵ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ΨһҪ����ǣ���д��һ���ֿ�ʼ�Ͳ�Ҫ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㹻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1989�괺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䣬��ʿ��д�����Լ��ĵ�һ�����硶���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֪��ôдϷ������дһ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䣬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˵�Լ���ʱ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籾���绰һֱռ�ߣ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ʱ�⣬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ʿ�л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ص�Ӱ�졣���߹�����ۺ����Ĺ۵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ǿ�ҵ�д���嶯����ۡ���ׯ�������ǻ۲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ӳ��ͻȻ�Իĵ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ִ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µĸ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ᰮ����Ĺ�ʿ�о���д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û�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ҵ�ͯ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ඥһ�㣬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ɫ�ʵ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ѡ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磿
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߹�ʿ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˺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ڸ���15����ߺ�42��ʱ�ٴ�ת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һ����硣����Ϊʲô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ػش𣺡�Ϸ������鹹һ�����磬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ʵ�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Լ���ܸߵķ�
�����ڹ�ʿ�п�����Ϸ�粻��һ�鹩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Ϳ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ʵ�ϣ����ǡ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걾�ʵIJп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ǩ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ȸ����ĵ�Ӱ����硣�º��ⲿ��̫���ճ����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Ӱ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Ϸ���ġ�ͷ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ɢ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ʱ��ǡ����1989�굽1994��֮�䣬�Ǹ��Σ��й��ով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η粨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ȴ�ָе�ij�����ε�ѹ�֣���д�ľ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ɵ�һ�ֿ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ְ�Ŀ��ת���Ϊ�ĵ�Ϭ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˴����ı�Ե�����д��Ϸ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Ц˵�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ˣ������꡷�Ŀ����ò�خѡ�ˣ��Լ���ֻʣ�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᳡��д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Ա����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ǡǡ���ǰ�ƽ���˾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̨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ô�ݶ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᳡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һ�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˷ܵ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Ȥζ�ԣ������ûȤ�����Ǿͱ�ŪϷ��û����Ϸ���ˣ��㻹д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Ū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ɷõ��죬���ʹ�ү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㣬��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Լ����ٴ�ת�У���Ϊ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Ը�����ĺܶ࣬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˵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Ҫֵ��д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ǰ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һ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ʧ���ɣ�һ��ͦ�á�
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Աʲô�����Ը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ɫ���ͦ����˼�ġ������ͻ��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˽��ˣ�ͦ����˼�ġ�����һ��Ϸ���ԭ���൱�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ڸİ���ͷ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ȥ��11�£���ʿ��ִ���ĵ�һ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ݣ�����ɫ�ĵƹ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̨�Ͽ���һ�ʱ��Ϳ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Ǩ����ʿ��˵��20��Ϸ��Ҫ�ǰ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״�ģ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ʱ����̵Ľ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ǿΣ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Ӱ�ġ����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ַ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ٷ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£����ص�ЦЦ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ľ籾�Ҵ�80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ܸߵķ֣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˵����Ϊ20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Ե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£���˵�Լ�Ҫ���Ŀλ��ܶࡣ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̫�٣������ù⡢��̨���֡���Ա֫��ѵ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·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Ҫ���е����ݣ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ʱ��̬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Ϸ�����ڲ�Զ�Ľ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ү��Ц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ζ�����ƣ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ۺ�ö࣬���൱���ڱ���ǰͷ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�˵IJ����ϣ��þ��˺Ƕ���ţ���
�ؼ��ʣ�

- ���·���
����
- �Ƽ�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+���ս�˹���ˡ��ٷ����ܡ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�20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è3���ϼһ�
- 01-30�°���̸���װ�˹�� ��ӰӦЧ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е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¿ƻ�Ƭ
- 01-30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˹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
- 01-30���Ҵ��Ժ���ں����Ϸ��̨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硶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 08-26���ݵ�ͼƬ��Ӱ��
- 04-29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Ϸ�ĵ���
- 12-17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 2019���⻪��ʫ�贺
- 02-19����
- 08-02���[��]
- 10-2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
- 02-11��һ�캣�⻪��ʫ�贺���ڶ���
- 04-232019���Ľ��мӹ��ʵ�Ӱ�ھ籾��
- 03-20��Ӱ[Ӣ]
- 06-26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

���ڱ�վ - ��վ��ͼ - ��Ȩ���� 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- ��ϵվ��
Powered by Pacificarts Info
Code © 2013-10 Pacificarts Inf
Copyright@http://pacificartsinfo.com all rights reserve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