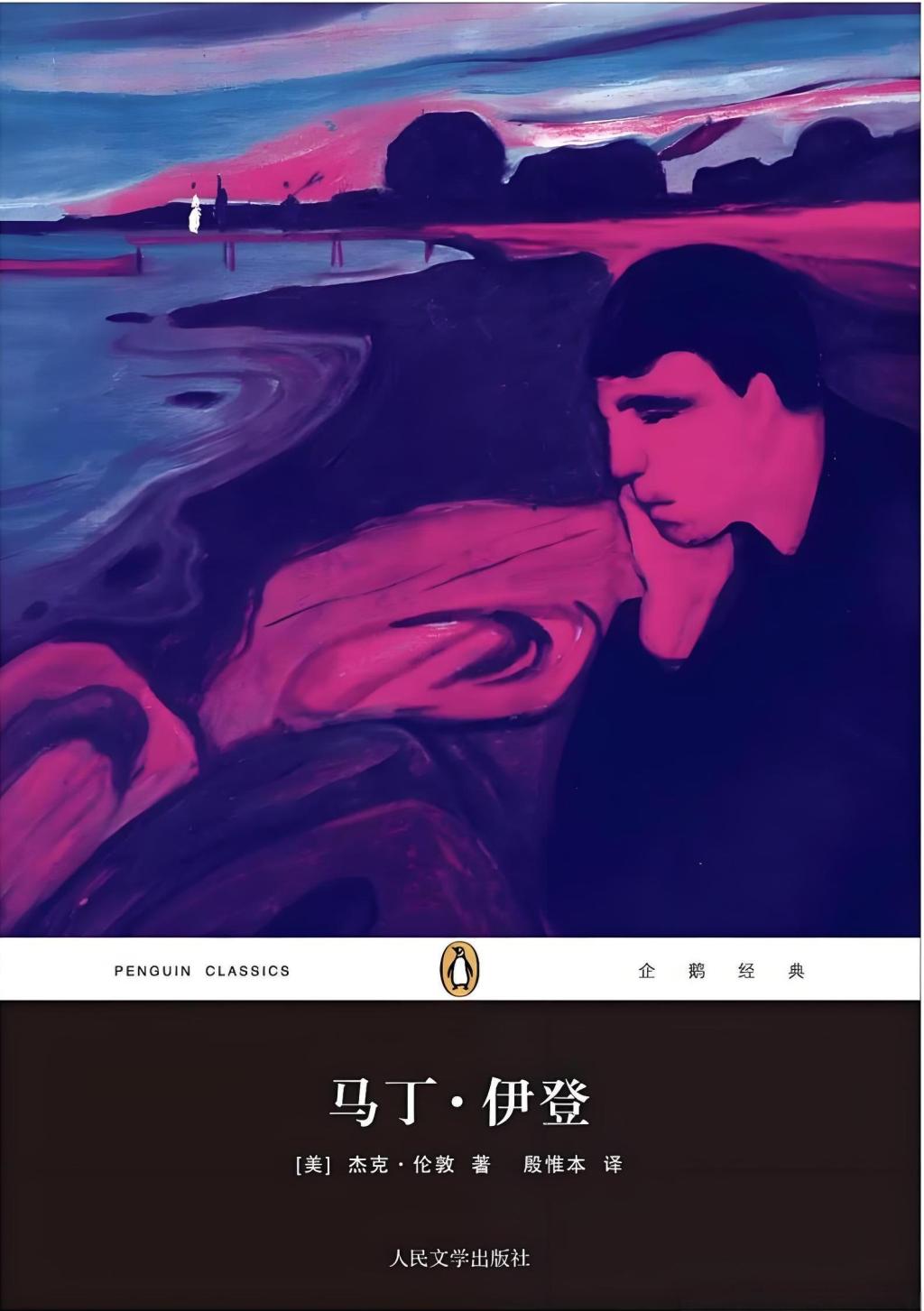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
���ɵ¡����𣺶�С˵�Ȳ�����
ʱ�䣺2018-09-20 12:15:50 ���ߣ� 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 ������2018��09��19�� ���ɵ¡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¥ľ�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ŦԼ��ѩ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Ľֵ��ϣ���ǰ�IJ�ƺһֱ�̵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е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�һ��ո�µı��ۣ�һ���ɵĴ��ڳ�ͣ��·�ߡ������贩������ɴ����ǰ�ȡ�����IJ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..2018��09��19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2018��09��19�� ���ɵ¡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¥ľ�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ŦԼ��ѩ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Ľֵ��ϣ���ǰ�IJ�ƺһֱ�̵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е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�һ��ո�µı��ۣ�һ���ɵĴ��ڳ�ͣ��·�ߡ������贩������ɴ����ǰ�ȡ�����IJ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..2018��09��19�����ɵ¡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¥ľ�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ŦԼ��ѩ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Ľֵ��ϣ���ǰ�IJ�ƺһֱ�̵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е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�һ��ո�µı��ۣ�һ���ɵĴ��ڳ�ͣ��·�ߡ�
�����贩������ɴ����ǰ�ȡ�����IJ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ɳ���䲣���輸�������ɵ¡�����ס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̦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ռ���ȸ��ë����Щ�ڷ��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ȸ��ë�Ļ�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Ŀ��װ�Ρ�
���ǵIJ²�õ���֤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еļҾ߶�����ͬһ�칺�����ʹ�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д�š�л��̽�á��Ļľ�ƣ��ֵ����ܻ���һȦ��ɫ�ͳ�ɫ���۽�ë�����Ӿ���ɴ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ѵ绰�߰ε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Ҿ��Ǻü��졣
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ڶ�¥��һ���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ʰ�øɸ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һ�ࡣ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κ�С���衢װ��Ʒ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ղؼң��Լ���Ʒ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
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һ��ţƤֽ�ļ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С˵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ȡ��ijƪ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ڰ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ǽ��ˢ���˰�ɫ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ǽ�ϼ���ʲô��û�ҡ����ߴ��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εĴ���б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
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׳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ߴ�����ӻ�ţ�п㡣���Ĵ��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˵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ͳ��ͺ��첻�壬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ǹ�һ����͵ô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ͣ�����ᷳ���ʡ�ʲô��ʲô����
�ɷ�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Ű�һ�굽һ�Ű˶���֮��ͨ���ż���ɵġ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л��̽�á������Ӳ�û�йҳ������ɷù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ѩ�Ǵ�ѧ��ѧ��˳·���ݷÿ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ĵĶ��ӡ�
�緹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ڻ�ʢ���ݺ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㡣���ͼ����ն����Ի�ʢ���ݡ����Dzɷ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����˹�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Ǽƻ�ÿ�궼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һ��ʱ�䡣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Ӹ����Ǽң����ش������û�У�ס���Ķ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Ī�ȡ�����ɭ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ȱ�
һ�Ű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ɵ¡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ģ���ʲô��ʹ�㿪ʼд���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ڻ�ʢ���ݶ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ﳤ��ġ� �����ھ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ﱾ��ά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ƽԭľ�ĸ־⡣
ĸ�������ۻ�Ա��Ů�д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ڼҴ��ţ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ɲ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ǵ��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⡣���ڳ���ˮ���·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ƿ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ҩˮ����ÿ���糿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Ҹ�����ҩˮ����ʿ�ɡ���ͨ��Ҳ���Ǹ�ˮ�ص��·�����һƿ��Ҫ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ѷ�ľ�ĵ������
�ǵ���һ����͵͵�س��˳���һ���Ҳ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ļ���һ��С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
С��ʱ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һ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С���ӡ����ܼ�ס�ĵ�һ�䷿�ӿ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ļ��У�����û�в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ʱ�Ҵ�Ű��ꡣ��ͨ���ڰվ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°�ؼ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һ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Լ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һ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һ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Ѿ�֪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˰�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Ⱦ�ȥ�ˡ�����Ȼ�ǵ�ĸ�ס��Һ͵ܵ����ųԷ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ͷ�ľ������ա�

���ɵ¡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ʹ��д�����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��Ψһ�����ǣ��Ҹ����ҽ��˺ܶ�����ʱ�Ĺ��£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游�Ĺ��¡�
�����游�μӹ��ϱ�ս�����潻ս��˫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ߣ��Ϸ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ȥ�˱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̡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Ц��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ô��Ϊ��
��֮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ҽ�һЩ���£���ʵ��һЩû��ʲô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·�ϵĶ�ԡ�
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̿���͡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״νӴ�����ӲƤ�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β����࣬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һ��û��˽�˿ռ�ļ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˽�ܵ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ܵĵط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Щż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�˽�ܵIJ��ֺ��Ķ���һ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ŵ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ȥ�ɵ���ʲô�ɡ���
�ţ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к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ȥ��Ҳ�Զ��һ��СϪ���㡣�Դ�һ����ҿ�ʼ��ҰѼ��Ұ���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ܵ����顪�����Ժ͵��㣬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д�Ķ�����
�Ƕ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࣬�����ѵ�һ������ʷС˵�����桤˹Ƥ������̽С˵�⣬���Ƕ���Ұ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Ұ��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ˡ�
��д��һƪ�ܳ��Ĺ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ܷ�����ô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̨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С˵���ѿ��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˳�ȥ���Ҽǵ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־�Ŀ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ַ�����ǰѸ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Ҽҡ�λ�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ݲ����µķ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ƪ���ӣ�ȥ���˱�ĵط����г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ϣ���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棬��һ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һ���ɹ��˵����ң��ڸ�һ�����ֽ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�ѧԺ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顣�и����¸���ƻ����ȸ�ʮ����Ԫ��Ȼ��ÿ��ʮ�黹��ʮ��飬һ�����껹����ʮ�꣬����֮һ�ɡ�ÿ�ܶ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Ҽ���˼����¡�
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ˣ��Ҹ�ĸҲ���ٸ�Ǯ�ˡ���ĬѧԺ�ܿ�����˷��ţ�˵�����һ�ΰѿ�壬����Ȼ���Ի�ý�ҵ֤�顣���ƺ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跨�ø�ĸ��ʣ���Ǯ�����ˣ��Ұ�ʱ�յ���֤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ǽ�ϡ�
���ڸ����ڼ��Ҿ��϶��һ��ڱ�ҵ��ȥ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ںܳ�һ��ʱ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ֹ������ұ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æ���Ұ���һ�ݹ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ھ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Ҳ�ϲ����ݹ������ӵ�һ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ӡ���һֱ�ɵ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·��ˣ��ʹ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顣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ô��С˵����Դ��ʲô�أ����ر���֪����Щ�ͺȾ��йص�С˵��
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Ȥ��С˵Ҫ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һƪ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ⲻ�ö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һЩԪ�ء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ģ����ܻ��ǹ��µĴ����㡣
�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⽫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ʥ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仰ʱ�Һ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ܾ��Ժ����ҽ��˾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仰��һЩ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棬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ҹ�˼��һƪ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˹̩��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ڭ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ٺͰ��ݡ�̩�յģ�����ij�̶ֳ��ϵ��Դ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ܴ��ҡ�
С˵���ܳ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Ѩ���硣 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ڳ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졣�ڰ��ɻ��ǣ�����һȺ��Χ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ij�����ϵ�һ�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ڶ����糿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䣬����Ů���ÿں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侵���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İְ֣�����뿪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ע��ԭ���ǡ�D-e-r-e daddy����СŮ���ѡ�Dear��д����Dere�����Ǹ�ƴ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ォ��D-e-r-e daddy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�˴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Ҽǵ�������һƪС˵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ܿ��ܣ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Եġ���
��Ȼ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һ�У���ij�̶ֳ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ʡ��Ҷ��Դ���С˵һ��Ҳ�����С�ǡǡ�෴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ˡ��ǵ�˹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ˡ��ǵ�˹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ƪ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Ҳһ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˵�ġ���ķ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˹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С˵�dz�ͷ��β���Դ���
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С˵ʱ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㹻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йص�һ�ж�˵������
С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д�Լ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ҷdz����вŻ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Ĺ��¡��Ǻ�Σ�յġ�
���ҵ�д���ַ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һ��Σ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ֺܴ���ջ�һ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Ϻ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д����

���ɵ¡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ϵ�д���С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ʱ��ÿ�춼��д��һ���һ�죬���ָо���á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ʲ������˵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Ҳ�д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һ��ʱ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ûд���κζ���һ����һ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С�
��Ⱦ��һЩ��ϰ�ߣ����ϲ�˯�� һ˯��˯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ûʲô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ͺ͵ȴ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ǰ�ͱ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йأ��ҵ�д���Ǽ�Ъ�Եġ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ʱ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ͻ�д�Ϻܾã�ʮ��ʮ����ʮ���Сʱ�� һ���һ�죬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Ǻܿ��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Ҵ�ʱ�䶼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д���档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һƪд�õ�С˵����һ��ʱ�䣬Ȼ�������дһ�顣дʫҲһ����д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Ű����ij�ȥ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ϼ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ŪŪ������ĸģ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
С˵�ij��廨����̫���ʱ�䣬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ξ���д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ȷʵ��Ҫ����ʱ�䡣��ƪС˵��д�˶�ʮ�廹����ʮ�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ʮ���壬��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IJݸ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˹̩���Ű��û����̵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ϲ���ĵ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ӣ��Ҳ�֪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ѡ�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д�˰˱�֮����Ȼ�ڻ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д�ú��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ˡ�

���ɵ¡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Ա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Ӱ�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֪�����Һܻ�����һ�㡣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̵ĸı䣬Ҳ��ʲôҲ�ı䲻�ˡ�
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˫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ǰɣ�����˵��ij�̶ֳ��ϣ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˵��ֻ�Ǹ���ͬ�ġ���θ�һ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
�Ҳ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ξ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һ���ͻ�ǰפ����һ�ײ����˵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ƻ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ֵ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Ტ�۵ģ���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һ�ָ������֡�
����ô���д����Ҳ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Ҽǵö�ʮ����ʱ���ڶ���˹���ֱ��ľ籾������˹•����ʩ��С˵������˵�ʫ�裬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п˵����ֺͿ��˵�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˹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ʻ���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ı�ĸо����㲻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Ǹı䣬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Ҿͷ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ı䣬��һ��Ҳ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ֱ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Ǯ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ݳޣ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Һ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κ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ᡣ
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˵ʲô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ͷ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•����ɭ˵��ÿ��дһ�㣬��Ϊ��ϲ����Ϊ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Щ��һƪС˵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�ܸı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۵����Ӽ�ʹ�й���Ҳ�Ѿ�һȥ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д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״���µ��ض���Ⱥ��С˵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�õ��˽⣬������Ҳֻ����һЩ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Ϊ�ġ�
ʫ��Ҳ����ͬ��̦˿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ţ�˵��Щʫ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
��С˵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ģ��Ҿ��ã���Ҫͨ��С˵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ı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ϵ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Ⱦ��㡢��Ⱥ�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ı仯���첻����
���ң���Ҳ����ΪС˵Ӧ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йء�С˵����Ҫ���κζ����йأ���ֻ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ҵ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Ķ���Щ���ò�˥��Ʒ�����ṩ��һ�����ã�Ҳ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â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Ϣ��
��̸��ɾ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¼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ҷ�̸1����
�ؼ��ʣ�

- ���·���
���λ��- �Ƽ�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+���ս�˹���ˡ��ٷ����ܡ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�20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è3���ϼһ�
- 01-30�°���̸���װ�˹�� ��ӰӦЧ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е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¿ƻ�Ƭ
- 01-30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˹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
- 01-30���Ҵ��Ժ���ں����Ϸ��̨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硶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 08-26���ݵ�ͼƬ��Ӱ��
- 04-29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Ϸ�ĵ���
- 12-17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 2019���⻪��ʫ�贺
- 02-19����
- 08-02���[��]
- 10-2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
- 02-11��һ�캣�⻪��ʫ�贺���ڶ���
- 04-232019���Ľ��мӹ��ʵ�Ӱ�ھ籾��
- 03-20��Ӱ[Ӣ]
- 06-26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