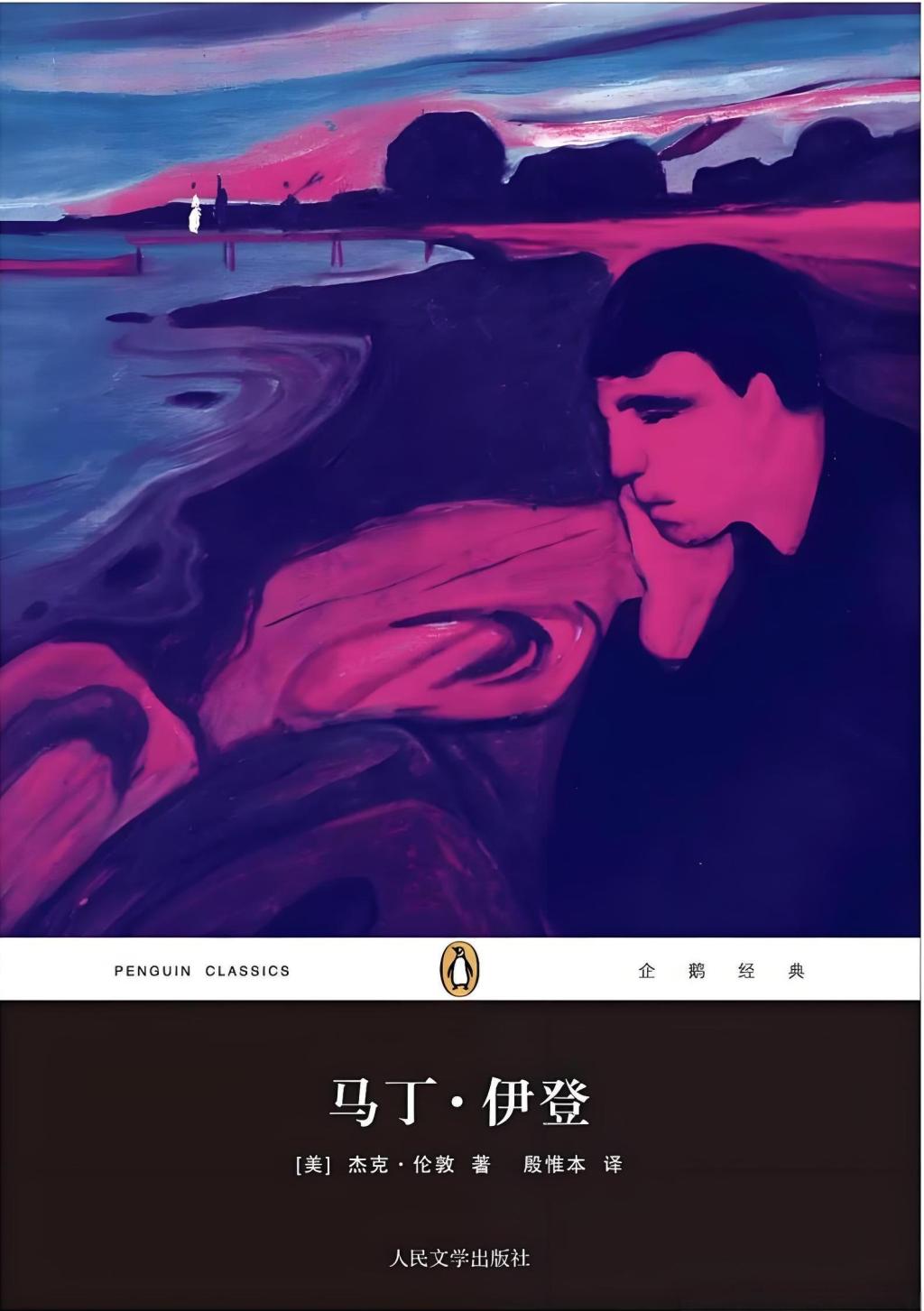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
���||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
ʱ�䣺2018-01-20 13:55:00 ���ߣ� 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о� ������2018-01-15 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о� WeChat ID fanyiluntanIntro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..2018-01-15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о�
������2018-01-15 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о� WeChat ID fanyiluntanIntro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..2018-01-15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о�WeChat ID
fanyiluntanIntro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㽶���棺
2017��10��23��
��Ǯ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ʫ��ε�һ�ֵ���
���� ǰ�� ����
���ѵõģ���Ϊ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Ե�ʣ��ڱ����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ʦȴ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Ǯ�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ȷ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Σ�ͬ�еĻ���ʫ����Ұ���Լ��͵��Ķ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ң�ÿ���˴����Լ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ʦ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ܴ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Լ��IJŻ���Ҳ���ڱ�¶�Լ������ۣ�Ȼ����ȴ��һ�����Ͻ��ı��ֺ�ʵ�٣�����ѵõĻ��ᣬ��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
����λ��ʦ��ͬ��Ҳ�Ǻ��ޱ����ģ���ʫ���д����ʫ��ķ��뵽��ѧ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Ƕ��Ǹ��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ǫѷ��̬�����ڻش�ģ��ر��DZ�����ʦ��һ�겻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ʦ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˴�ʫ���ѧ��֮һ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Ķ�ѧ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꣬Ҳϣ���Ա���ʫ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벿�ֻ�����ʫ��ε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贴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ͬѧ��Ħ��
���Ǵ�һλʫ�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ʼ��һ�����硰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1936���֮�շ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ס�һ�Ŀ�ͷ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ʫ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���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̨��ĸ�װ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ش��ִ����Ҹ��װ�ĵڶ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γɺ�嫵�����ķ粨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д��ʫ��ĸ����Ѳ���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ʮ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ĵƹ��¡����ɡ��Գ�һ�ָ߹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��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졷������ͬѧ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һ��ʫ��ʼ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Ĵ�һλʫ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û���հ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ʫ�������¿ռ䣬ͬʱ������һ�ֹ۵㣬Ҳ�����룺
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Ӧ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ʫ��ת�Ƶ�ʫ�ˣ���Ϊ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룬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硣ʫ�˴��µ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˵�ݷ���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
ʫ�˱�ʫ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Ҫ��ʫ�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ƪ��ḻ����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ע�ţ����ע�ŵ�ȻҪ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˻���Ũ�ҵ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Сʱ�ڻ�ñȶ�ʮ�껹��ʵ���飬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һСʱ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ô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Сʱ������ͬѧ�Ǿ���ʲô�췭�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أ��ⲻ�DZ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ʱҲ��ƽӹ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֮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壬���·����ë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һ��Ȩ��ǰ̧����һ��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ּۻ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ϳ��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ѧ�Ƿ�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ͨ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Լ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ڰ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ʫд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ͬѧ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Ҳ�Dz�֪��ߵغ��˵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ھ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ɴ˸ı䡣���ڵ���ͬѧ�ǵ�ϰ��ʱ���뱱��ͬϯ����һλʫ����ҰҲ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Ѿ�����ڷ�̸���ἰ��λ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д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û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ʱ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ʼ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ʫ�ж��ٽڣ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߶��ԣ�����Ҫ�ľ��ǽ��ࡢ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Сʱûѧ��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ѧ�ʵ�����ѧһ�ϲ�ͨ�����һ��ر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һ���ỻһ����һ��ģ���Ȼ��ȫƾ�о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Ұ˵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棬��ʱ���Ǻ����⡣���ܿ��ҵ�д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״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ţ��Ȿ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磬1996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Ĵ���ԭ��ժ�����£�
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ֻ��һ�ֿջý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Ļ�Ľ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ʱ���ӻ����ҵ�ͷ�ԡ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ò��ʮ���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ִ�ʫ�к����õ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ijЩ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Ӻ�Ĩ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�Ҳû��ʲô����֮���ˡ��ռ�����ħ��ʹ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ʫ��ʮ�����ڵ�ǿ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Ĺ��룬��ͨ��ȷ�б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ɫɫ�������빦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֤���ڶ���֮���ͻ��Ӧ���DZ��뽨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ЩƬ���Եĸ�֪ʹ���ܹ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Ʒ��ˮ�����ɵؽ���Ӧ�þ��еĸ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ʾ�Եij���ȵ�д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ľ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ҵij�˼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ദ����ʫ��ɢ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λʫ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ϵ�̸��ң�Ժ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ʫ�����ԵĴ�����кܴ����Ծ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ײ�������ھ�ʽ�ı仯�ϣ��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㹻����Ϊ�ǿ���˵�ǡ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ŵ㡪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Ŀռ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ɢ�ĵ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�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Ҳ���ڸ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ͬѧ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е��Լ�дʫ���Ͳ�β��ɻ�Ļظ���
��ʫ��ɢ����ȶ��Գ�����ʤ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û��ɢ�ĵ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ɢ�ĵ���Щ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Ҫ���ʾ��һ����Ȼ��ͬ�ľ��磬������ʫѧ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
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ʱ���õ�塷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⣺����һ���ݽ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ʫ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ʷ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֣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Խ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йٵ�ȫ�濪�š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߸�˹��Ϊʫ�˵Ĺ�Ȧ��Խ�ǿ��ܾ�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Ρ����˶�ʮ���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Ȧ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һ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Զ�д����սʤ�߸�˹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ϯ�䣬̸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壬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Զ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ܶ�ʵ�飬���Ǻ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ϵ������˵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ġ����翴���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ʹ���ˣ���ɱ�ˣ���Ϊ���ߵ�̫Զ�ˡ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Ǻ����Լ�ʹ��ĺڰ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ɢ�IJ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ں�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Ϣ�വҲ�������ֻص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룺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һ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γɡ�һ�����γ�ij�ַ�Χ�����־ͱ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ʫ����ͼȥ��һ�ν��ҵij�Խ������˽ӽ���Ȼ�Ĵ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ΰ���ʫ��Ҳ���ѵִ����ִ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ź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ʫ�Dz���д�ģ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ڲ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Ƕ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Ұ��ǰ��һ�η�̸ǡ�ɹ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ϵļ������⣺����Ӧ�ý������ʶ��Ҫ�ҵ�����Ľ��ࡢ��Ϣ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ʫ�跭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á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õĴ��⺺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ɺ���չ�����ֱ��ǣ�ʫ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Ϊ����ĺ��
���ڷ��룬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'���'���飬��Ҫ�ͺ�ѧ�ҳ������룬�ٺ�����ʫ�˹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Ҷ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ʫ�Ĵ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˺ܴ���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ĵĶԻ���ϵ�ĸ��ܣ��Ҷ���ͼ����ˡ���Ҳ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顣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ǰ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˽⣺�������ࡰ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Ϊʱ���ϵ����û�ж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ˡ�ʱ���õ�塷���ض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Բ����䷳��ϸ˵���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Ķ��Ǵ��Ķ���ʼ�ģ��ֵ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仰��˵��Ҳ����Ū��ʫ���뷭��Ľ��ޡ�һ���õ��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뱾�����ǣ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Ƥ���ǡ�Ȼ��Ϊ����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ʫ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ƺ�Ҳֻ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ʯͷ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ȷ��Ϊһ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˴ֱ���ȱ�����ĵ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Ǽ�˭��˭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֪����Ȼ��̸�����Ļ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ʱ���õ�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漰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ȴʮ�־�ϸ��λ�����ֲ�ʧһ��ʫ��Ӧ�еľ���֮��â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ʢ�ޱ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¶�ʩ��ķ�Ķ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·�һ�¾Ͱ����¶�ʩ��ķֱ���Ƶ��ҵ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ģ�û���˱����Ǹ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뱾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̡���ʫ�˶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ʫ�ˣ�1972-1978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1970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꾫���ϵ�һ���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ֵ��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Ļ�Ʊ�������괵��һ���·硣�漴��һ����Ƥ�鴫�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ӹ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ġ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ϵ�Э��С˵���ż��ˡ����ʻ����С˵����ܽ�ػ����¿��ŵ�ʱ���Լ���·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Ļ�Ƥ�飬��Ҷ��ͼ���д�ġ����ӹ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ټ������ǰ�ʮ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ٷ�ʫ�ˣ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ڶ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˵��ձ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й�ʫ��ת���й��ŵ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ͼҹ��黳��һ����Ҫ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Ϊ����
���й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֣����˵�һ���䣬��ʮ���ֻ��ʮ�˸��֣��Ϳ��Դ�Խ�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ɽ�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г��ֳ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ʫҲ�ܴ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�ѧƷ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黳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��ȫͬ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ԣ�Ҫ�ﵽ�ڴ����ȷ��ͬʱ���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̶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δ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ⷽ�����÷dz��á���ҰҲ˵�����ڹ�ʫ�У�ʱ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ʱ��Ϳռ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й�ϵ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е��õ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һ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֯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ͬѧ����ᵽʫ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ͬѧ�ǵ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ϸ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Ծ���Ϊʫ��֮�����̸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Ӷ��ָ���һ��ʫ�д��ڵ����⡣��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ʫ��ϵͳ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ָÿ��ʫ�˶���һ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༰�ô�ϰ�ߣ����ı��˵�ʫ���Ⱦ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ϰ�ߡ������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ɶ�����ͬʱҲѧ���˱��˵�ʫ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Լ���ϵͳǿ���ڱ��˵�ϵͳ����õ��IJ�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ǵ��ģ���Э���Է���ʵ�ڶԷ���ʹ����д��Ϊ��ȷ����Ҳ��ʫ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Ի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˵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��Ϊһ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̲Ľ����˷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ô���ͨ����ʽ�ϵ��Ķ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ʵĹ�ϵ��ͨ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ת�������任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塣˵������ÿһ���ִ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ſ��ܽ��롣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ң�Ҳ�����Ŵ�����αʫ�裬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࣬��ʵ��ȫ�����롣��ϸ���ļ����£�һ��α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ܣ�����⡣��ֻ��ͨ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α���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ɹ��ݾ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ı����ⲿ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���˥�䣬���ṹ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ѹ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ݱ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Ϊһ�ְ����ı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Ҫ�ġ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ʱ���õ�塷�������꡶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Σ���ʵ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ɾ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Կ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ɡ���ʱ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ʶ�ʫ���¼����ʱ��ͬ�ĸ��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ٴ죬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ʦ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һ�㣬���˾�㤡���
��ҹ�����漣��
�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ڶ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š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룩
ҹ�����漣����ô���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㿴����ĶԻ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̾�����뱱��һ�����뵽���Ļ���С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Ȱ�ʫ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㯵�һ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Ψ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к�������ʲ̹ķ�����Ǹ��˵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ƾɣ����Բ�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ͷ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ֺ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ӱܹ��һ����ıȱȽ��ǵ��Թ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һ����˥�ϣ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ͺ���Դ��еģ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ȴ��Ȼһ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䡶���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ֶ���˹ʽ�ĶԿ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Ƕ�һ�����ƺ�ѹ�ֵ�ʱ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飬Ҳ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ʱ���Ĵ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ƽӹ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ΰ�����Ʒ֮��/�ܴ���ij�ֹ��ϵ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ĵ��⡱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ڵ����֡�
��ͬ���ݽ��У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־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Ӳ��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ǽ�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Ĺ�ϵ����ν�����ϵĵ��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ġ�ָ����ԭ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ɫ�ʣ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Դͷ�������⡯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�˵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ڵĽ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ĵ����ܽ�Ϊ���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ָ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Ľ��Ź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Ȼ�ᴥ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棬��ô�����ϵĵ��⡱ָ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ĸ��֮��Ľ��Ź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Ź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Ҷ��Լ��ġ����⡱��
���ֵ��⣬�ÿ��Ѻ�ʫ��ʫ����Ȼ�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Ұ˵�������ѻ����ǿ���ѹ�������澭�飬�����˱�Ȼ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ʫ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ʫ�˷Ŵ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ע�Ķ������ô�ͳ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ҹ��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еĻ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ĵ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Ȼ���кͿ��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̸һ̸���ĵ���Ŀ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ֻ�����¶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Ǯ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��ӣ�ֻ���㽶���档�����Ƕ�֪���Ǹ��㽶����ͬ�ԣ����п��ζ����ʵ�顣���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ۣ��㽶��Ƥ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Ӳ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Ψ��ʫ�����㽶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׳����ѵ���ζ����ij�ֲ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ʫҲ���㽶���滯ѧ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θ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ʫ�˵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��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Ҳ���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ѵ�ʫ�˵�д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ͨ�й��˵IJ�ɣ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б��ѡ��Ҳ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ֲп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ʫ�й�ע�˼���Ĵȱ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ﻭ��
���Ϊ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ܶ����˵İ��ߣ��ᴩ�����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Ρ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д�£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Ȼһ�������ڵȴ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ҵ�ڵȴ���һ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Լ����ڵȵ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Ҳ�ߵ���ͷ��
����Ұ�Ļ�����ɢ�ġ�һЩ���̣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Ľڣ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ˣ�ֻ�����Ż���ȥһ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䡣�˿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˰�¥�ϵ�һ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ȳ��ϵĴ�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ѩ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ݶ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ҵĴ��ϡ����һƬ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ѩ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Ʈ�����·�ҪƮ���ҵĴ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ɫ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е㳬��ʵ�ĸо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Ǿʹӡ�һЩ���̣�һЩ�����Ŀ�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ôҲץ��ס��ȥ���˺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ʫ�����ʮ�£��ҵĻ���ֻʣһЩ�о���һЩ��Ϣ��ʫ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ڷ�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˷����γɺ�嫵�����ķ粨�������γɷ籩�����Ƿ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졢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ƪ�����漣������ð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�ʶ���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ƪ������ʮһ��д�꣬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µĺ�ҹ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ʫ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һ��ʫ��ʼ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һ��ʫ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��ô�ܹ�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٣���ôдһ��ʫ����Ұ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ˣ����Ҳ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ܹ��Ӳ�ͬ�ǶȽ�����ô�ܹ�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һ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Σ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棬�ֻ�����
̫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ҹ�Ю��
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һ���Ŵ�ľ���ǰ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ɵ�
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Ϊ�Ҷ���ò���
ׯ�����£�
�ҵ���֮�أ�
��û���γɾ����Բ���ʡ�
��ͨ����ʽ�ĵ�·�ϣ�
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һ���˿��Ѻͳɳ��ķ��
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Ψһԭ��
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Ϯ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ƽӹ��
��Ұ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ģ���Ϊ����ʫ�裬��ʵ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Ҫ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壬�ر��Ǻܶ����Լ��ǿ����ʫ�ˡ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�Ǻܺõ����壺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ij��ʫ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档
��һ��д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һ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壬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̬�ȡ�Ψһ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Ҹ��˵�ϰ�ߣ�ʫ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ǣ�����֮�⣬����Ҫ��ʵ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Ҹ��˾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�һ�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һ��ʫ����ã��dz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ľ�����ɣ�Ҫ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õ�ʫ��һ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и��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ָо���ȷ�Ļ����ܹ���Ϊ�dz�����˼��һ��Сʫ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뵽�ˣ����ǻ���Ҫ��ĥ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Ƚ�һ�µġ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俪ʼ���Ҿ����ر�á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泩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֮��Ĺ�ϵ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ɽ�ɡ������۹������Ǽ�Ѻ�ϡ�β�ϡ�ͷ�ϡ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ʵ�Dz�̫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ǽ��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ԡ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ϵ��
��ʽ�Ҿ��øտ�ʼ��һ����ͼ�ġ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ıȽϳ����ڶ��αȽ϶̣��ر��ֿڡ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�Σ�ׯ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֮�أ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Բ���ʡ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֣���Ȼ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ϣ��е㻥��Ť����˵��ʱ����˵���ĸ����ԣ���ʵ���ﲻ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Ұ���Ҽǵ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д��֮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û���κ�һ�����͵ľ��ӣ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��н��࣬�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ģ���ʽ�Ѿ����ˡ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���棬���Ǻ����⡣���Ǻܿ��ҵ�д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״̬����дһ��ʫ֮ǰ����ʽ�Ѿ�ȷ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ȣ����ӵĽ��࣬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һ�䣬�dz����ݣ��滺�����ǵڶ���ͻȻ�Ϳ�ʼ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Сʫ�������ֱ仯�Dz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dz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ͬ�Ķ��䣬��ͬ�IJ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й��Ŵ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ʽ�ģ���ʫ���ִ�ʫ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û��һ���̶�����ʽ�ġ�Ϊʲôʫ�˾��ø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ߴʣ����ǰ���һ���Ϳ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˵��ÿһ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Dz�һ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ܲ��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ֳ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ʵ��ʽ��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Ľ���ͽ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˵����֮��Ĺ�ϵ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˳��ɢ�ĺ�ʫ����ȫ��һ����ɢ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A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˳���γɵġ�ʫ�Ĵʺʹ�֮���кܴ����Ծ�ԡ�����˵�Ļ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ԣ���žһ�£��кܴ�ı仯�ˡ�����ʵ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Χ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贴���Σ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䣬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⡱����imag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ġ�
д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Ӿͻ��ˡ�����ǰ�ƽ�����ʽ�ı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鷢���˱仯��ÿһ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ܴ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ܶ�дʫ���˲�֪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Ԩ���㲻�������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пռ䣬��һ�䵽һ�䣬��ɢ�ĵĸ��ֻ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ŵ㡪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Ŀռ䡣
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㲻��д̫�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㹻�Ŀռ䡣�ռ�Ҳ�dz�Ĭ��һ�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滭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Ȼ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Ҫ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
��Ұ��ʫ��Ҫ�ڷ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ʱ�ա���ʫ���ķdz��á�ʱ�ո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ʱ��Ϳռ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й�ϵ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е��õ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һ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֯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Ҫ��ʫ�Dz��ϵضѽ�ȥ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ʫ�ˣ�����˵Ҫд��һ��ʫ��Ҫ֪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Ҫʲô��ʫ����һ���ֲ������ĵġ���ʮ����ǰ��С�º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һ���ֹ���ȥ��С��˵��ɾ���ɡ���˵��ԭ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İ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һ���ֶ����ܸġ������С�¹����ڻ�һ���ӣ��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Ⱦ������ó���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ﵽ�����ȷ��ͬʱ�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̶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δ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飬����ϵ��һ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ر�
дʫ�жϵ�ʱ���кܶ����⡣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Ϸdz���Ҫ����Ծ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̽�գ�һ����Ԩ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Ҫ����Ҫ�Ķ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Ƴ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Ĭ��ʫ��Ҫ��ԭ�㣬����֧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ʱ�䡣��һ����ֻд�˺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ѧ��д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ʼDZ��ĸ����һЩ�Ƚ�����Ķ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ܹ���ʮ����ʮ�궼���á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ʽ����˵A��B��C��D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C�ĺ�Ӧ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D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ı仯���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ࡣ������Բ����ظ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Ҫ�ҵ��Լ��ķ��
���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д����ʱ���õ�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ʱ��ĸ����Ҫ�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ܶ�������ɵġ��ܶ�ʫ��д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ô��û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ֹͣ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Ĭ��ʫ���ӹκ�����ͻȻ����ֱ���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뵶/����ʼת��/��ת��Խ��Խ����/�ɳ�ΪһƬ����/�ɳ�Ϊһ��ֱ���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չʾ�Ŀռ䡣
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һ��ƽӹ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ΰ�����Ʒ֮�䣬��Զ���ڹ��ϵĵ��⡣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ʲô�ܶ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꣬��Щ�����ǣ��ܶ��ʫ�ˣ����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�и��顣���ǵ��ճ�����û�д̼���û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˵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ź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д��ӣ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ձ�����⡣�Ҿ���ȷʵ��Ҫ���ѣ���Ȼ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Ҫ�п��ѣ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翴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ң������ô�ҡ����ĸ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���꣬�Ϳ�����ֱ�ӵĹ�ϵ��Ҫ��Ȼ���ѡ�
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ͬѧ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ῴ���ܶ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ν�Ŀ��ﻯ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��Ū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ϻ�ʫ��С˵����ļ��ɺ��Ͷ���û����ô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ȥдС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˭������д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ĸ㲻���ף�Ϊʲô���IJ��á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û���ش𣬵��ǣ�ÿһ���˶�ʫ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̬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ɡ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ҵĻ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ֵ��һ���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ʮ����дһ��ʫ�����Ҿ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дʫȷʵ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ʽ��д����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ڵ���д���Ĺ����У���Ҫ���룬��һ��ʱ�䣬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ѣ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ȥ�ˡ����̫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û���ж�һ��ʫ�ı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̫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ʫ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䣬�����ҵ��жϡ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û����¼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ҵĽǶȵ��жϡ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ʫ�IJ��֣��й���ʫһ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պ��ʡ���־Ħ�����࣬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Ҫ�Ĵ�ͳ�����ǿ�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ʫ�ͺ�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ǣ��ܶ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ʱ����д���档
д��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�ô�죿
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Ҫȥ̫ǿ���Լ����ҵ��õ�ʫ���õ�ʫ�ˣ���ʦ��̼��㣬�Ķ���д���ǽ����ƽ�еĹ�ϵ���Ķ��Ĺ����л�ͻȻ�ܵ�Ӱ�졣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Ҫһ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ഺ�ڵ�һ�����̡�
��ô��һ��ʫ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Ҫ֪�����Ե�ʲô�̶Ⱦ��ã����Ǻ�ʫ�˵�����ҪͻȻ��һ�����룬�ӱ༭�ĽǶ�ȥ����
дʫ��θк����в���ô�죿
��Ұ��д����ʱ��Ҫ��ȷ�Լ�Ҫ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Ҫ˼���ñȽϳ��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��ĵ�ij�ֳ嶯���;۽�һ��Χ�����Ǹ�ȥ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ǿ�е�д���ͱȽ���һ�㡣
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෴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ά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С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ղ�˵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壬���ǵ��Զ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ܶ�ʵ�飬���Ǻ��ѣ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˵�����ǰ��ֽ���һ���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ˡ��Ҿ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ϵ������˵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ġ����翴���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ʹ���ˣ���ɱ�ˡ���Ϊ����̫Զ�ˣ����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�Ǻ����Լ�ʹ��ĺڰ��ľ��鶼��ϵ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ϲ��ʲôʫ�ˣ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棬����ʫ��̫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Ǹ���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ֿ����߸����ǡ���ʱ��Ļ�Ƥ�飬��д�����ӹȡ���Ҷ��ͼ��ơ����ǿ���˵�Ǻ����̵ģ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
ʫ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ϲ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Ҳ���к�ʫ����
��Ұ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˴�С�;����˺ܶ࣬���ȱ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١��Ҿ��ÿ��ѻ����ǿ���ѹ�������澭�飬���ұ�Ȼ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ʫ��һ����Ҫ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Ϊ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й�ʫ�˾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и��۵㣬�Ǹ�ɽ����ģ�˵��ʷ�Ѿ��ս��ˡ�����ŷ����һ��ʱ�䣬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ûʲô̫�����顣�����ر˵Ĺ�����˵ĸ���ȥ��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䣬���Եģ����Ҳ�ܲ�̬�Ĺ�ϵ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ʱ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ǻ��и�����ĵģ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ɡ�Ȩ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⣬�ȵȡ�
���ǶԿ����м������⣬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ڿ���֮�С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鵽ijЩ����֮��ʫ���Ǻ����еģ��ܷŴ�ܶ��Լ��ĸ��ܡ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ǿ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ʫ�˷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ū��һ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ע�Ķ������ô�ͳ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ҹ��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ֶ������еĻ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ĵ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Ȼ���кͿ��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Ⱳ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֮�⣬��ѧ��ҵ�Ժ���һ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һ��࣬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Ǿ��ǵ��Ӵ������ʱ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뿪�Ժ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㿪ʼ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䣬�Լ�Ҫ�е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Ρ����й����ôӾ�ʮ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ν���г�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ʫ�˺ö�Ϳ�ʼͶ����ᣬ�ܸ�ʲô��ʲô���ܵ�Ҫ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У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�Ҫ�ҵ�һ�ֺ�����ͽ�ķ�ʽ�����ԾͿ�д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ŭ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Ǹ����ӣ�����һ��̬�Ȱ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ʣ���ʵ����ѹ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ࡰ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�ǿ��Է��֣��͵����й�ϵ����ս�Ժ���ѹ�Ⱥ�ì�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Ǿ��ö�ŷ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û��ʲô̫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ж��ܶ�ʫ�˺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Կ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ѹ�ȣ���Ҳ�Ǻ�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�����DZȽϺ�ƽ��ʱ�ڣ���ʱ���õ�塷�Ÿ�ʫ�ˣ��Ƕ�ս�Ժ���ٵĺ�ʫ�ˣ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Լ��ĽǶȿ��ġ�
���Ҷ�����С˵Ҳ��Ϊ���С���ʵ����ʫ���ر�࣬�ܶ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û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Ҳ�Ǻܴ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⡣
���ڷ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Ǻ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й��Ļ�����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ǰ�Ӱ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Ҹղ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ˣ����ǵ�Ӫ�����Ǵӷ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ܵ��ܶ��Ӱ�졣�������кܶ����⣬��ʱ���õ�塷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ǰ�ڡ��ջ����أ����˺ܶ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˶�ʮ������ߣ���ʵ�Ҿ���Ҫ��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⡣��ʵ��Ҳ˵������ֻ�Ƕ���Ӣ�ġ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֤�����ҵ�ʱ�ǶԵġ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Ǯ���кܶ����⣬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Ρ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Ĵ�����һ��Ҫ���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飬�ͺ�ѧ�ҳ������룬�ٺ�����ʫ�˹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Ҷ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ʫ�Ĵ������Ҿ����˺ܴ���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ܸ��ܵ���Ӣ�ĵĶԻ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ͼ����ˡ���Ҳ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ʵ�顣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ǰ�ߡ�
����
�� 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ҵ�Сѧ����ϰ����
���ҵĿ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
��ɳ����ѩ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ж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
�����пհ���ҳ��
ʯͷ����Ѫ����ֽ��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ڽ�ɫ��ͼ����
��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ڹ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ڴ��ֺ�ɳĮ��
����ľ��
����ͯ��Ļ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䣬�кܴ�ı仯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ҹ�����漣�ϡ����أ�̫�����漣��ûʲô��
�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Ի���ϵ��ƽӹ�Ĵ�û�����塿
�ڶ���ļ����ϡ���ô���ľ��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Ƭ��
��̫����ù�ij����ϡ���һ�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Ұ���ڵ�ƽ����
�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Ӱ�ӵķ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ÿһ�Ƴ�����
�ں����ڴ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ɽ���ϡ�̫�����ˣ�ɽ��ô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ƶ����ĭ��
�ڱ�����ĺ�ˮ��
�ڳ��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ڸ���ɫ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ѵ�С·��
����չ�Ĵ����
�ڷ��ڵĹ㳡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ڵ�ȼ�ĵ���
��Ϩ��ĵ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ھ��Ӱ��ҵķ���
һ��Ϊ���Ĺ�ʵ�ϡ��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Ӱ�졿
���ҿ��籴�ǵĴ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̰�Զ���ѱ�Ĺ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צ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Щ��Ϥ����Ʒ��
�ڵõ�ף���Ļ����ϡ�ע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Ĺ�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Ӧ�ʵ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ǵĶ�ͷ��
��ÿһ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ϵ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ھ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
��רע���촽��
�ڸ߳���Ĭ�ĵط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ұ��ٻ��ı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ҷ��յ�ǽԫ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䵭��ȱϯ��
�ڳ���Ĺ¼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ݵ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ģ�һ���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ڻָ��Ľ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ʧ��Σ����
��û�м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ƾ��һ���ʵ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¿�ʼ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ʶ��
Ϊ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ɡ�һ��ʼ��ʵ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��һ���Ķ���ij����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룩
��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ڣ��貵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ʦ��Ϊ���ǽ�����һ��ʫ��Σ��ܿ��ܣ�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ѿ�����ӣ�Ҳл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ǫѷ�����̬�ȣ�ϣ����һ�죬�����л����Ϊ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ࡰ���д��顱
�����д��顱�����ȴ���̫�ɡ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ꡢ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ơ�����ʩ�͵¡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Ĭ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߰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���ķɡ�������Ѧ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ȡ�
�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룬���д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¿��ǣ����ȣ��ڹ���ʫ���뺺�����ߵ��ı�����֮�У���Խ���Եı߽磻������Զ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ս��Ϊ�ḻ�ִ������ṩ�µ�Ʒ�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ʫ�ˡ����ߺͶ���֮�䣬���ı���Ӧ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Ӧ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顱
һ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ʫ��
һ�ʻ�������ʫ���ͼ
��Ӣ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ճ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װ���տڴ���
ʫ��֮�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ȷ����
ת�ԣ������Ļ�
�ؼ��ʣ�

- ���·���
- �Ƽ�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+���ս�˹���ˡ��ٷ����ܡ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�20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è3���ϼһ�
- 01-30�°���̸���װ�˹�� ��ӰӦЧ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|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е�5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¿ƻ�Ƭ
- 01-30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˹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Ƭ��
- 01-30���Ҵ��Ժ���ں����Ϸ��̨ ����
- 01-30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�硶�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01-30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Ա�㱨�ݳ� ����
- 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- 08-26���ݵ�ͼƬ��Ӱ��
- 04-29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Ϸ�ĵ���
- 12-17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 2019���⻪��ʫ�贺
- 02-19����
- 08-02���[��]
- 10-2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й���
- 02-11��һ�캣�⻪��ʫ�贺���ڶ���
- 04-232019���Ľ��мӹ��ʵ�Ӱ�ھ籾��
- 03-20��Ӱ[Ӣ]
- 06-26�����